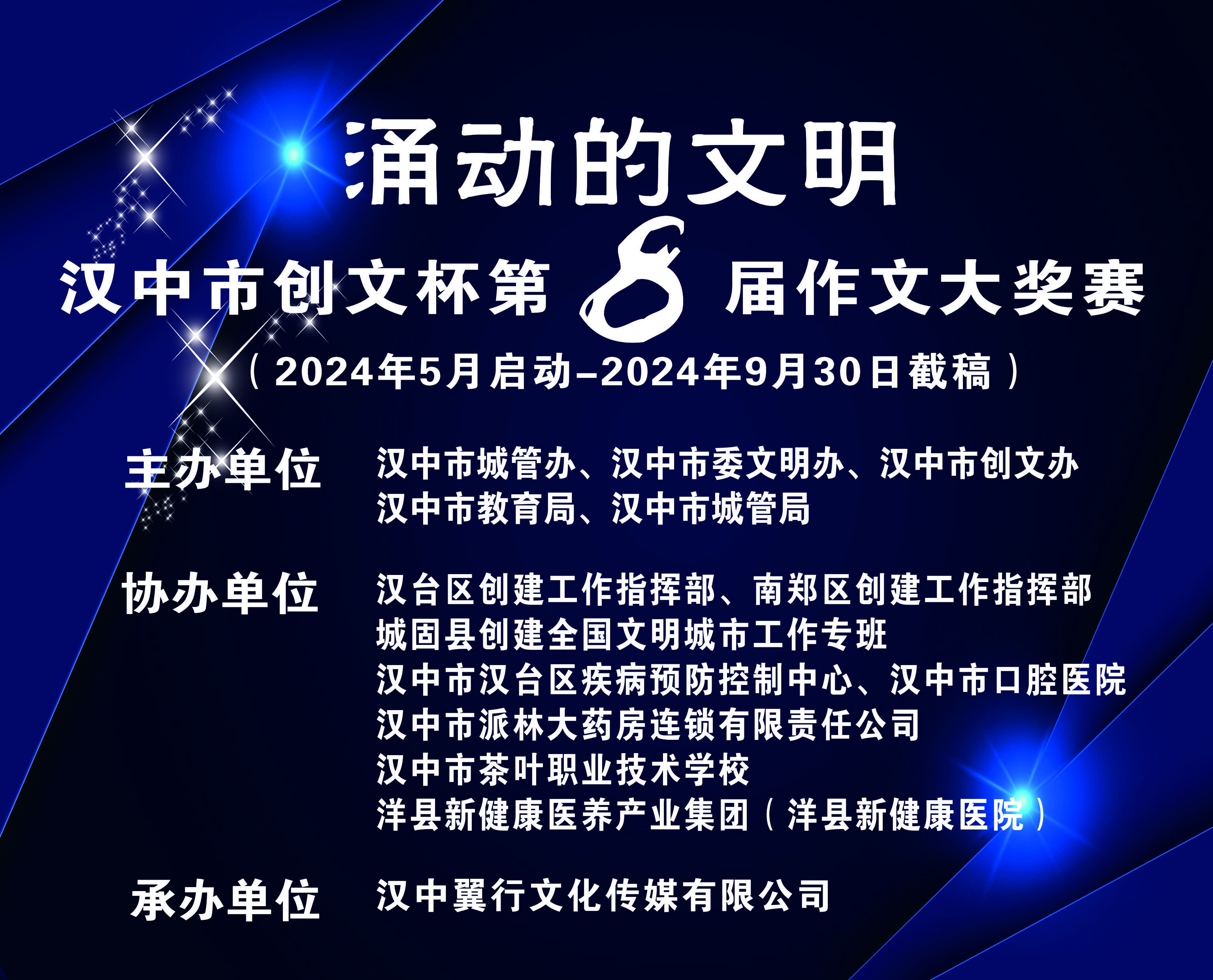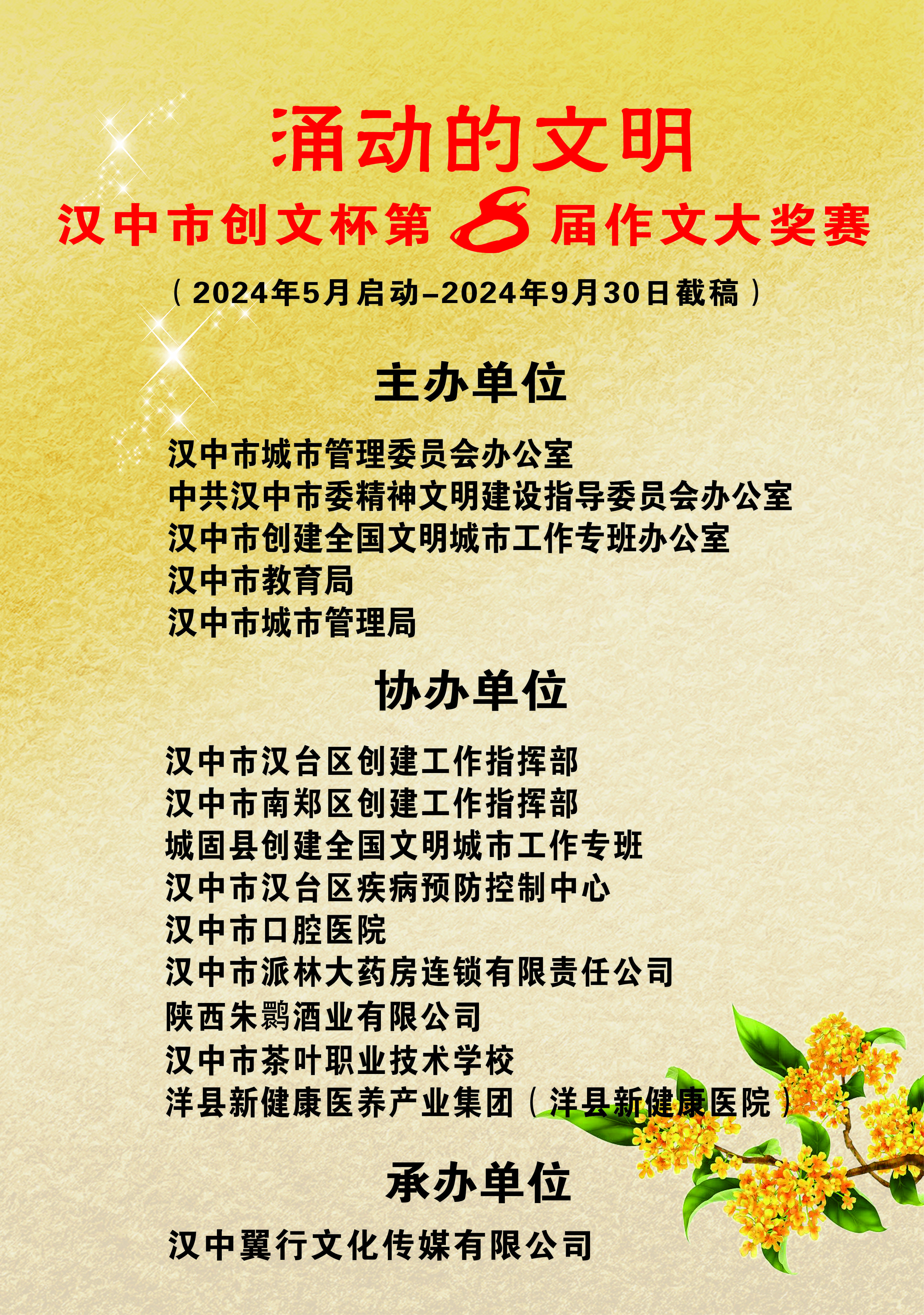诗人刘诚:人性极境的深层突进
——评刘诚诗歌和他的第三极神性写作
【江南大学】何根生
当一批伪先锋诗人趾高气扬、企图独霸诗坛、建立欲望书写的一统天下的时候,刘诚及其第三极诗人群,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当代诗歌界树起了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大旗。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出场,惊扰了大小伪先锋诗人的好梦,诗歌界一时天下大乱,声讨刘诚的檄文铺天盖地,蔓延十余个诗歌论坛,对刘诚进行人身攻击的贴子在网上随处可见。刘诚似乎犯了弥天大罪,他的存在成为罪恶的象征。此时的刘诚除了正常上班,还要每天投入大量的精力参与论战,应对各路伪先锋诗人及其理论家的辱骂与恐吓。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随着第三极文学运动的深入,这场对第三极神性写作的疯狂围堵和颠覆,最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第三极之横空出世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第三极神性写作有纲领,有理论,有创作,各路诗歌英雄风云际会,纷纷奔来其间,远非一般诗歌乌合之众。时至今日,第三极神性写作风生水起,已经在诗歌界站稳了脚跟,越来越呈现出严格意义的诗学流派气象。而那些曾经对第三极进行疯狂围堵的网络流氓却集体失踪,用刘诚自己的一句诗来说,就是:“失踪得比逃跑还快”!
刘诚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就写过诗歌、长诗、诗剧,进行过多种形式的文学试验。刘诚当时在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是我的学生。当刘诚把一篇有关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的剧评拿给我看的时候,我不禁眼前一亮,深为学生中有这样新锐扎实的文学评论感到吃惊。这篇万余字的大块文章,洋洋洒洒,文采飞扬,博得了同学和老师的一致好评。据说在同一时期,刘诚还写过一部三幕的大型爱情诗剧,该剧按照戏剧理论中“三一律”的要求构思,以文革初期的武斗为背景,表现一代青年在非正常年代爱情与政治的冲突,人物性格鲜明,剧情推进有力,到高潮时几位主人公全部死于非命,悲剧色彩极为强烈。但在那个年代,“文革”一直是文学创作的禁区,这部规模宏大的悲情诗剧,当然也只能在同学中小范围传阅,刘诚没有拿给我看,最后也只有不了了之。从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刘诚被分配到当时的陕西工学院工作。这所颇有名气的工科院校坐落在褒河镇,该镇距离汉中城区三十里地,是汉中以北的重要门户,附近不远就是书法历史上稀世瑰宝“石门十三品”的诞生地,又是著名古道——褒斜道的出口——汉王刘邦用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历史壮剧就发生在这里;也正是在这里,因为苦于蜀道之难,古代地方官员上奏朝廷,动用三千刑徒,用“火烧水激”之法,开凿了闻名中外的“石门隧道”,在世界交通史上首开隧道用于公路交通的先河;再往上不远,就是古代第一美女褒姒的故里,解放后国家又在那里筑坝,建起一座大型电站。故而褒河一带,高山兀立,大河奔流,道路笔直,人烟辐辏,自然风光瑰丽,地理人文资源极为丰厚。但文学是这样一种看似容易而其实风险极高的事业,业余玩一玩也许不失风雅,只是千万不能当真,要当真则必得付出代价,否则定然一事无成。刘诚那一届有过很多热爱文学的青年,其中一些一样很有潜力,后来都从其中退出了。自离开母校以后,刘诚有很长时间没有回过母校,在我们这一面看来,刘诚也许会像大多数学生一样,只能以教师职业终其一生了。出乎所料的是,刘诚独秉的文学才华却在这一独特的环境里得到发育——正是在这里,刘诚“灵感爆发”一发而不可收,不声不响地写下最初一批先锋性诗作,其中尤以长诗《走向人群》为最著名。以这首惊世骇俗的抒情长诗为主体的处女诗集《走向人群》1986年出版,得到了国际知名艺术家、文学和国学功底都十分深厚的东方艺术大学教授范曾的“激赏”,刘诚也因为这部书的出版,成为初露锋芒的知名青年先锋诗人。此后由于生活动荡,加以对诗歌和文学的恶劣环境深感失望,刘诚“复仇式”地诀别诗歌和文学,我也从当年任教的汉中师范学院调任江南大学,从此失去了联系。然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何况一别就是漫长的十三年!到2003年再次联系上时,刘诚——这位命途多舛的杰出诗人,已经以5000余行长诗巨作《命运·九歌》而名扬天下。又一月,我收到了刘诚从陕西寄来的厚厚两卷本《刘诚作品》。其中,散文集《在命运里旅行》所收全是大散文。刘诚写散文不过偶尔为之,并没有执意要为当一个散文家而写作,但几乎篇篇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刘诚散文的优点就一个字:真。真感悟、真性情、真思考、真才情、真识见。这是一部极少水分的散文集。在散文领域,散文家多如牛毛,不乏矫情和卖弄,小情趣、小哲理、小感悟所在多有,很少有作家能够这样在散文中呈现自我、坦露胸怀。通读全书,没有一点文人的酸腐和轻薄,这样的作品,非真性情中人而不能为。而厚达490多页的诗集《愤怒》,携一大批精美的抒情短诗和长诗力作《命运·九歌》横空出世,令“兽性写作”(刘诚语)淫威下颓靡腐烂已久的中国诗歌界为之震惊!中国诗歌界险些埋没了杰出的诗篇,这是中国诗歌乱象的罪恶。在兽性写作走红的时候,这样的诗歌必然被遮蔽,兽性写作垄断了诗歌流通的命脉,阻断了伟大作品走向读者的通道,但这恰好从反面佐证了刘诚写作的超越时代的价值。
兽性写作这一次很可能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强劲对手。而在新时期以来、尤其是第三代诗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兽性写作可谓一马平川,几乎没有遇到过任何对手,相反它受到欢迎,得到了资本和权力的默许。版面是他们的,批评是他们的;兽性写作家族人丁兴旺,永远不愁绝种,因为深藏在人性深处的兽性蠢蠢欲动,对兽性写作的登场,一直有强烈的期待。由于时代道德水平的总体下滑,人们想要“娱乐至死”,同时天真地以为可以“娱乐至死”;兽性写作的声音,淹没了人性最深处对于神性的微弱呼唤;在这样的总体时代氛围下,兽性写作得到了快速成长,从而盘根错节步步深入,在我们这个国家登堂入室,侵入了这个国家主流文化的核心部位,并在那里生根开花;从北京到外省,大量的文化传播资源被兽性写作力量侵夺。只是月满则亏;天令其亡,必纵其狂;兽性写作猖狂到一定程度,必然有另一种相反的写作出来进行矫正,此为天道。由于第三极神性写作的出场,这一切开始逆转,至少在刘诚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逆转的努力和希望。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走向,刘诚洞若观火,其人虚怀若谷而又内心坚定,且最少思想框框,不信邪,不惧怕兽性写作势力的淫威。在刘诚身上,我们看到智慧、才华、担当、坚定的品质、清醒的头脑,我们看到很多,却看不到丝毫的油滑,看不到老气横秋的暮气和懒惰,以及诗歌界最常见的随波逐流和得过且过、卖身投靠。刘诚一直处在自我突变的最前沿。难怪在2004年10月,当刘诚向诗歌界捧出厚厚一部最新诗集的时候,要把它命名为“词语的暴动”,其实多年来刘诚一直在自我“暴动”,随时为诗歌界准备着爆破的能量。刘诚是那一种最不可小看的诗人,有刘诚存在的中国诗歌不会风平浪静,随时都可能出现奇迹。回望整个诗坛,在五十年代出生的诗人里面,能够坚持诗歌写作的诗人已经寥寥无几,而能够越写越好、越写越深刻、越写越能写、才气永不泯灭、在众多兽性写作势力的排挤围堵下一直在为当代新诗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如刘诚这样老而弥坚、大器晚成的诗人,在当代中国仅此一例。这是当代诗歌的幸运。我敢说,当今一些自以为得计的兽性写作代表诗人远不是刘诚的对手,事实上刘诚也从来没有把这些人视为对手。作为诗人,刘诚对土地和人民的熟悉,对底层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的熟悉,对生活和苦难的洞见,在中国当代诗歌和诗学理论方面挺进之远、之深,实绩之丰赡厚重,总体写作的道德含量,都是任何一个骨头轻贱的兽性写作诗人无法比拟的。我们时代的伪先锋,在刘诚那里完全没有市场,反而不时遭到无情的嘲笑。在中国当代新诗里,刘诚首开以诗论诗的先河,而又论得机智和精当,很多这样的诗篇令人拍案称奇、忍俊不禁。在《我与先锋调情》这首长诗里,作者嬉笑怒骂,对伪先锋的倒行逆施,报以高度的轻蔑和冷笑,因为他看出在伪先锋的外壳里,“装满了稻草和鸡毛”,此外什么也没有。刘诚知道人民需要诗、诗更需要人民,在任何时代的读者群里,都会为伟大的诗歌留下必要的空间,相信自己接近真理远胜于论敌。诗是什么?诗不是废话,不是畜生淫声浪语的杂乱堆积,也不是败家子貌似激进而实则非常有害的自虐和自渎。你把屎尿涂在脸上,你用刀在脸上划出了很多道血口子,你就“革命”了、“先锋”了、“高深”了?只怕远不是这么简单。“诗是诗人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刘诚斩钉截铁地说道。从形式上看,诗是精神的私秘的产物,是一种带有个人信息的声音,往往烙印着个我的印记,但从本质来看,这声音绝不是凭空而来,且必与人类和世界的状态切切相关。刘诚心里清楚,除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热情,自己手中捧着的是一大批“使人变得可爱而不是相反”的诗歌作品,而“先锋的车箱里装满了过多的私货”(刘诚诗句)。
第三极及其神性写作概念,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具有极大包容性、生长性的创造,是诗人刘诚对当代诗歌的杰出贡献,是他奉献给时代的一组有血有肉、注定要影响深远的新词!
什么是第三极,什么是神性写作?熟悉新诗进程的人知道,中国当代新诗是从新时期开始复活的,朦胧诗正是这一复活的典型标志。然而好景不长,朦胧诗刚刚从一场大争论中缓过神来,还未及开花结果,取得应有的实绩,第三代诗歌已经携风起云涌之势,以文化复仇式的强烈冲动,将朦胧诗予以埋葬。正如一些论者所说,第三代诗是以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反宏大叙事、反传统、反崇高为特征的,并以此种反叛的姿态,颠覆了朦胧诗歌运动。由此看来,第三代诗已经表现出浓重的文化虚无主义色彩,通过对朦胧诗的颠覆,实现了诗歌对良心和道义等传统因子的剥离摘除,为欲望写作打开了闸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诗歌界都处在这种文化复仇式的狂欢中。如果不是海子异军突起,这一段时间的中国诗歌,除了欲望书写,势将一片空白。这种状况在海子以后继续加强;随着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确立,诗歌写作中的欲望写作急剧膨胀,越发暴露出兽性的一面。一些作者要么对人性的弱点和丑陋一面讳莫如深,要么对这些东西视若桃花,津津乐道,加以欣赏和礼赞。在他们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无不成了欲望的巨人,精神的侏儒。但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艰难存在——它颠覆了朦胧诗写作的公共话语姿态,实现了诗歌写作从朦胧诗代时代立言的公共话语状态向个人话语姿态的转移,而又同时将朦胧诗作为时代良心和社会道义的独立担当精神作为宝贵遗产继承下来——这就是“英雄写作”,且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命运·九歌》。由于它的代表诗人刘诚在最关键的时候,一度退出诗歌长达五年之久,这一诗派只能一直处在地下状态,只是在2002年刘诚出版《愤怒》和散文集《在命运里旅行》之后,人们才窥见了它的冰山一角。正是从这个意义,刘诚说,神性写作是“第三代英雄写作的发育和成年”。
为什么要有神性写作,人性不是远比兽性高一万倍吗?从英雄写作到神性写作,其间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道理?仅仅是换了一个说法吗?对此,刘诚在《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一文中,有过大篇幅的精彩阐述。刘诚认为,当代诗歌里的欲望写作,已经大幅度膨胀为兽性写作,仅仅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式的“英雄写作”,已经远远不够了。“神性写作就是把英雄写作中与恶直接抢白和对话的荣誉收回,让恶再也听不到诗歌说什么,让写作构成恶的灭顶之灾,类似最后的判决,因而从整体上对神性感到害怕。在英雄写作那里,因为零距离对峙,恶还有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侥幸取胜,有时则是平分秋色,在神性写作这里,恶、任何的恶,都不可能再有任何机会,神性将恶完全排除,隔绝在神性以下。”这篇6万字长文这样写道。刘诚认为,“神性写作就是让真回到诗中,让善回到诗中,让美回到诗中,就是让博大、宽厚的道德感回到诗中,让真善美在诗歌里合一。”
第三极神性写作的提法,是对“文学要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一提法的历史性超越。文学固然要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问题在于人性通常很不可靠,首先人性并非“永恒不变”,相反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动之中,即使人性现在看着很好,谁也没有胆量为它的恒定不变担保。“文学写作永恒不变的人性”的提法,对于抵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强行入侵固然极其重要(曾被指为“人性论”受到长期批判),但是在文学本质的追问方面显得远远不够,反而极易为形形色色的兽性写作所利用,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兽性写作极易假冒人性狐假虎威,以假乱真,把诗歌搞乱。人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为善为恶自古没有定论。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性善与性恶,至今依然争论不休。应该说,他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但不完整,类似盲人摸象,因为他们都只是将他们看到的一面进行了强调,而将事物的另一面忽视了。人性是在路上的,是正处在“修炼”中的“半成品”(刘诚语),既不善也不恶,而是善与恶的集合。也即是说,人性不过是神性与兽性的一个集合体,至于究竟神性(善)大于兽性(恶),还是兽性(恶)大于神性(善),落实到个体则千差万别,完全看各人的具体修为和操守。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得失情势下,不同的人人性的善与恶并非总是一样,有时神性(善)大于兽性(恶),有时兽性(恶)膨胀到几乎完全掩盖了神性(善),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与缺陷。人性只是朝向神性打开了多种可能,并不等于神性,人性其实是神性和兽性对峙的战场,处在此消彼长的动态之中。人性中的兽性部分总是刻意对人性中的神性部分造成遮蔽,并拉动人性向兽性一面倾斜。总体看,由于人有短处捏在欲望手里,通常情况下都处在欲望的人质状态,所以人性一向是距离兽性较近的,如果拒绝“作功”(向上),则必然会一刻也不停地向兽性坍塌,有时甚至出现返祖现象(如二战中纳粹对于犹太民族的有计划灭绝)。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第三极神性写作的神性,与中世纪新柏拉图派的创始人、宗教神秘主义哲学鼻祖罗马人普洛丁所说的,“物体美是由分享一种来自神明的理式而得到的”,“神才是美的来源”的说法根本不同。神只是人的自身外在的显现,不是神创造了人,恰恰相反,是人创造了神,从对神的观照中,人获得了自信与慰安,从而更努力地去改变外在,创造新的外在。那种分享说、照射说,不过是割掉(或隐瞒)了人创造神的一面,突出了神影响人的一面,经过一些人的有意无意的宣传与夸大,看起来似乎是神创造了人,人分享了神的理式而得到了真、善、美,神成了真、善、美的来源。神性写作认为,神性不等于神,神性远远大于神,神性就在人性之中,是人性中最美好、且具有光辉的那个部分。当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占主导时,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作品中,都会出现乌七八糟的东西,而神性则不同,永远是美好的,是最高的星辰,即使处在一片漆黑的漫漫长夜之中,神性也可以为人生提供永远的指引,引领人性向崇高的境界提升,从而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将生存的价值最大化。神性也许不可能(也不必)将人性中的兽性摘除,把人都变成纯粹神性的载体,但却给人性带来希望,带来信念,带来向上的力量,带来真善美的光亮。神性写作主张人性向神性靠拢。刘诚说:“神性不是天外之物,就在人性的深处。”又说:“诗歌要有热,只能从神性来,因为只有神性一面,才真正关心人,从根本上关心人,不仅关心它的现在,更关心他的将来,既想到短暂的快感,也想到根本的福祉。只有神性的一面,才能确保诗人在任何时候都分清善恶、是非、真假、美丑。”神性写作承认人性的弱点与缺陷,直面人性贱的一面、丑陋的一面。刘诚说:“纯粹的人性很丑,几乎等于兽性,如果不加以修炼,是绝不可以成圣的。”由此出发,刘诚把神性写作概念一路向前向极限推进,不仅明确地界定了神性写作的概念,而且在与论敌的论战中,对神性写作的内涵,对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本质区别,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根本对立的原因、意义,及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神性与人性的关系,神性写作的缘源,神性写作的题材、实质与目的,神性写作与时代的关系,神性写作的价值、标准与力量等等方面,都作了独特的深入思考和精彩阐述。第三极神性写作主张,诗人心中必得有人民、有国家、有人类和世界,要有向上的信念。神性写作不仅不排斥个人的独特性,个人的色彩,个人的创造,个人的风格和自由写作,相反认为,艺术家只有在内心自由、美好和谐的心境中,才能发挥出聪明才智,显示出独特的光彩。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第三极主张继承我国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学传统,坚信诗歌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对诗歌遗产的批判继承。第三极无法容忍对我国从《诗经》、《楚辞》开始,一直到“五四”以后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以简单化、冷漠化、粗暴化、敌视化的态度,进行虚无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的全盘否定,反对披着任何外衣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包括诗歌遗产)的摧残与毁灭。神性写作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必须以同样的热情和态度去吸收和继承世界文化的精华,反对把整个人类的文化遗产人为地、硬性地分割成几块,分出等次排出优劣,从而用一部分去否定另一部分。
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根本分歧,也表现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神性写作认为,作品的目的在于揭示真理,净化人类的心灵,有益于提升人的存在价值;兽性写作却把写作看作一次发泄,把对作品的阅读欣赏,看作寻找刺激和快感的过程。神性写作认为,写作应当鼓励人把生存提升到崇高的境地,首先把自己的生存,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使鄙陋的生存具有光辉,并为此而不懈奋斗,有所作为。诗人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一目的去生,为这一目的去死,除了这一个目的,再没有别的目的;兽性写作则视写作为游戏人生的特殊领域,为一时、一地、为少数几个人,甚至一个集团博取名利的终南捷径。这样的写作,也可以产生诗歌,只是这样的作品,最终难以摆脱被淘汰与抛弃的命运。神性写作认为,教育人去爱的艺术,远胜于煽动人去恨的艺术,除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当千百万人难以生存,当他们看不到人生的未来与希望之时,作为诗人与作家必须对生存的真相作出指认。此时的作品,从表面看恨也许比爱多,但是从深层看,纵使是恨,它的最终目的与指归,也应当是为了爱,是爱的一种特殊达成。教人恨的艺术无法净化人的心灵,更无法把一盘散沙一样的人群团结起来,使人携起手来,去开创人类共同的未来。兽性写作则恰恰相反,他们以现世的名利为指归,从破坏切入艺术,教人破坏、教人憎恨、毁掉人类终极价值,教人越来越不知敬畏,是一种精神毒品,极大地扭曲人类的灵魂,是对人类根本利益的犯罪。正因为这些原因,神性写作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强调文学的道德背景和诗人健全人格的养成,把这视为诗人最重要的“诗外功夫”。刘诚说:“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连人也做不好的人,居然能够胜任诗人的高难度工作。”“诗歌的力量来自诗人的人格,是诗人的人格使诗歌强大和有力。”神性写作认为,没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根本不可能有神性写作;写作再特殊,也不能自外于人类向真向善向美的总体进程;那些“我成名哪怕它洪水齐天”,为了渺小的文学名利、不惜拉时代下水的伪诗人,应当以反人类罪受到审判,请他们坐飞机到二万米高空作自由落体(刘诚语)。
在当代诗歌界,刘诚是纯粹凭借诗歌创作的实绩和诗学理论的惊世骇俗赢得尊重的极少数诗人之一。刘诚不是灸手可热的行政官员,也不是文学杂志主编,可以在一个总是僧多粥少的诗歌场域里指点江山、呼风唤雨,连一个诗歌编辑也不是,且长期居住外省城市,不占有任何地理优势;在创办文学刊物《第三极》以前,连民刊主编也不是,手里没有任何版面,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大抛媚眼,把他当不得了的“青年领袖”看;刘诚也没有组织团伙,一向独往独来,在诗歌界没有任何呼应。同时刘诚又生为男性,长得也不算英俊,不像时下一些美女诗人,可以披着一张美女的画皮在中国诗歌界到处走动。刘诚只能以一位中国诗人的本色出场,以杰出的诗歌创造面对诗歌和文学。二十多年来,刘诚一直在老老实实写作,从来没有挖空心思去主编过什么年代大选、年鉴、各式各样的“中国诗歌一百家”、“世纪经典”之类的选本,顺便把自己塞进最靠前的某个位置。刘诚没有策划过任何这样的活动,这在一个要出台必得靠诗歌运动、诗人的名声大小可以与诗歌创作的质和量没有任何关系的特殊诗歌场里,是需要勇气的。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如此混乱和恶劣的诗歌生态环境里,刘诚居然完全凭借着诗歌及其理论的实力站立起来并浮出水面,这真的可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我敢说,如果脱掉了包装在外面的层层画皮,再将形形色色帮派领袖的背景完全抽除,当代诗坛没有几个诗人配和刘诚站立在一起。来自体制的强大资源,都被那些抢先一步占据要路津的“文学官员”垄断了,而你又不出来操作诗歌运动,民间诗歌运动这一块又丢掉了。刘诚占有最少最少的文学资源,却棒出了最多最多的诗歌和理论,是足以与北岛、昌耀、海子齐名的诗人。刘诚的诗及其第三极神性写作理论,应当列入当代诗歌史的一章,也应当列入当代文学史的一章,进入强制性的高等国民教育体系,进入可研究的范畴,现在没有列总有一天会列。这一点我在几年前就说过,至今更加深信不疑。刘诚是新世纪以来的时代氛围呼唤出来的诗人。这也是一种乱世造英雄;如果没有兽性写作二十多年的猖狂跳梁,人们难以看清当代文学病象的要害,正是兽性写作的自我膨胀和一超独霸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为第三极神性写作扫清了道路,准备了出场的舞台。从这里看,神性写作确如刘诚所言,是被“兽性写作逼上梁山的写作”。
越晚被承认的诗人越是有可能穿越更多的世代,因为他们的被承认,经过了更多时间的磨洗和考验。与后世的读者比较,当世的掌声和奖杯一钱不值,倒是非常值得警惕。那些抱团恶炒、为攫取当世的鲜花和掌声而不惜费尽心机的轻薄之徒,天天都想把自己与诗歌里死人的名字摆在一起,可是他们永远也搞不懂诗歌流传不朽的秘密机制。臧克家有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一历史的悖论,这一诗歌的饶口令式的秘密咒语,无疑是伪诗人的恶梦,量他们一生也难以摆脱。由于对刘诚诗歌极为推崇,自前年以来,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电话长谈。在电话里,刘诚一直为自己很晚出场而抱不平,引为一生恨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刘诚应当好好感谢各种原因促成的这个“很晚出场”。较早出场、少年得志,固然为人生一大快事,但很晚出场、直到很晚才得到承认,甚至被本时代完全冷落、而被下一个时代当作“文物”发掘,对一个诗人并不是什么坏事。杜甫就是很晚才被承认的。杜甫在世的时候,写文章称颂了他那个时代的很多诗人、包括长他几岁的李白,可是学者们在当时的诗人选集里,几乎找不到他的名字,更惨的是诗人在被他的时代整死之后,连遗骸也要在外漂流四十多年,这才被他的同宗侄儿运归河南故里入土为安。荷兰天才画家凡高终其一生,只卖出一幅名叫《红色田园》的画,如果不是靠弟弟提奥在经济上一再帮助,像他这样一个生性怪癖的神经质天才,很可能会被过早地冻饿而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以诗书簪缨之家,在写作巨著的后期,居然沦落到举家食粥的地步,巨著在后来是在度过了几十年的手抄流传的艰难历程,才最终登堂入室,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稀世瑰宝。诗歌和文学自有定数;在我看来,刘诚在2002年以后携一大批英雄写作诗歌作品出场,实在正当其时。用大历史的眼光看,第三极神性写作不可能比2002-2004年更早。一方面,以前的那个时代没有为它准备出场的条件,此前的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很可能是属于兽性写作的黄金时代,而不会为神性写作留下足够的份额,这也许就是诗运中的那一份神秘的“命定”,得认。另一方面,从个人成就的策略角度考量,刘诚也应该好好感谢命运对强烈出场要求的那一份不可抗拒的阻挠——用陕西话来说,正是得益于这一份不可抗拒的阻挠,刘诚这一笼诗歌的“馍馍”终于捂够了火候,避免了最容易出现的“夹生”现象。如果要吃弹性很好的“馍馍”,我们当然不能急于揭去笼盖,诗人自己也不要去揭,大家都得有足够的耐性——这是要吃好“馍馍”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的处理好处很多。首先是由于受到巨大的阻力,刘诚奔腾的才情一直处在蓄积中,避免了干涸,并由于多有阻碍,可以不时溅起拍岸的惊涛,生命得以展现出如此瑰丽多姿的神奇风光。喝茶不能一下把茶喝干,要留下“茶诱子”;好酒也不可一次喝光,而要尽可能留下一些,置之于瓦罐,藏之于深窑,假以时日,这样才会有上好的酒浆出场。才华是什么?才华有时也就是一股气;诗人最可宝贵的也就是这一口气,那是不可轻易一泄净尽的。唯其大器,只能晚成。如果一出场就走红,省略了蓄积发酵的过程,刘诚的才情很可能过早地一泄净尽——这就是大多数青春写作的可悲宿命。如果那样,将不可能看到《命运·九歌》那样拥有足够文学持久性支持的宏篇大构,也不会看到第三极神性写作的闪亮出场。而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正因为看到成名的好处,急不可耐地要求发表,过早地把最可宝贵的那一口气敞光了。在这里,长期的逆境对于成就大作家和大诗人,确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神秘力量。阻挠的力量越大,要求出场的力量也就越大,这样才有最深刻的体察,也才有话可说,正如一场棋逢对手的精彩博弈,缺了哪一方都不行。要说刘诚成功有什么秘密,依我看秘密就在这里。他心里有不平,有块垒,恰好在这个时候,诗歌走了上来。从这个意义看,任何自认为对诗歌的保卫都很滑稽,诗歌谁都不可能保卫,也不必保卫,中国诗歌自有自己的安排,它其实一直在那里等待着一个名叫“刘诚”的诗歌写作者,这个人没有辜负这份厚爱,他是努力的,他以第三极神性写作的理论和杰出实践,为我们这个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中的鲁迅的国家,也为此前饱受诟病的当代诗歌,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神性写作是人性极境中的深层掘进,反映着一批杰出的诗歌人拯救意识的觉醒,表现出这批诗人勇敢担当、舍我其谁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开创诗歌新局面的巨大理论勇气。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相信有相对真理的人不配称为人,而不相信世界上除了相对真理还有绝对真理的人,则不配被称为诗人,勉强去当,充其量也只能做成一个伪诗人。绝对真理是真诗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诗人追求完美、追求大善、追求至真,那是他的本性,是他活着、梦幻着、激情着、呼叫着的根本支撑。刘诚及其第三极诗人群不只是对相对真理有着执着的追求,而且坚贞不渝、满腔热情地去追求绝对真理,不仅有追求绝对真理的信念,而且有追求绝对真理的热情、勇气和行动。由第三代英雄写作,到第三极神性写作,他们诗写的方向,始终指向绝对真理——第三极那人类精神永恒的刻度!这与人类精神历程的根本指向是完全一致的。人类之所以虔诚地创造出三大宗教中的“上帝”,正是因为相信这个“上帝”,即是他们要追求的绝对真理,人类诗歌史上三部最伟大的不朽诗篇——圣经、佛经、古兰经,都是人类以最大的虔诚、最炽热的感情、最质朴深刻的文字,对各自信奉的绝对真理(上帝)的敬畏与礼赞。刘诚及其神性写作实践,是中国诗歌朝向绝对真理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集结和突进,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放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放在人类文化史这样的高度上,也必将产生广泛和深远的世界影响。
全中国一切不愿意看到诗歌全军覆没的人,都应当向第三极的文学大旗行注目礼,支付应有的敬意。因为刘诚和第三极诗人群的写作已经超越了渺小的名利;他们看得更高、更远,也更深刻;他们的诗学理想是:“让诗歌以王者的气度,统领起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刘诚语)。
2007.12.12,于太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