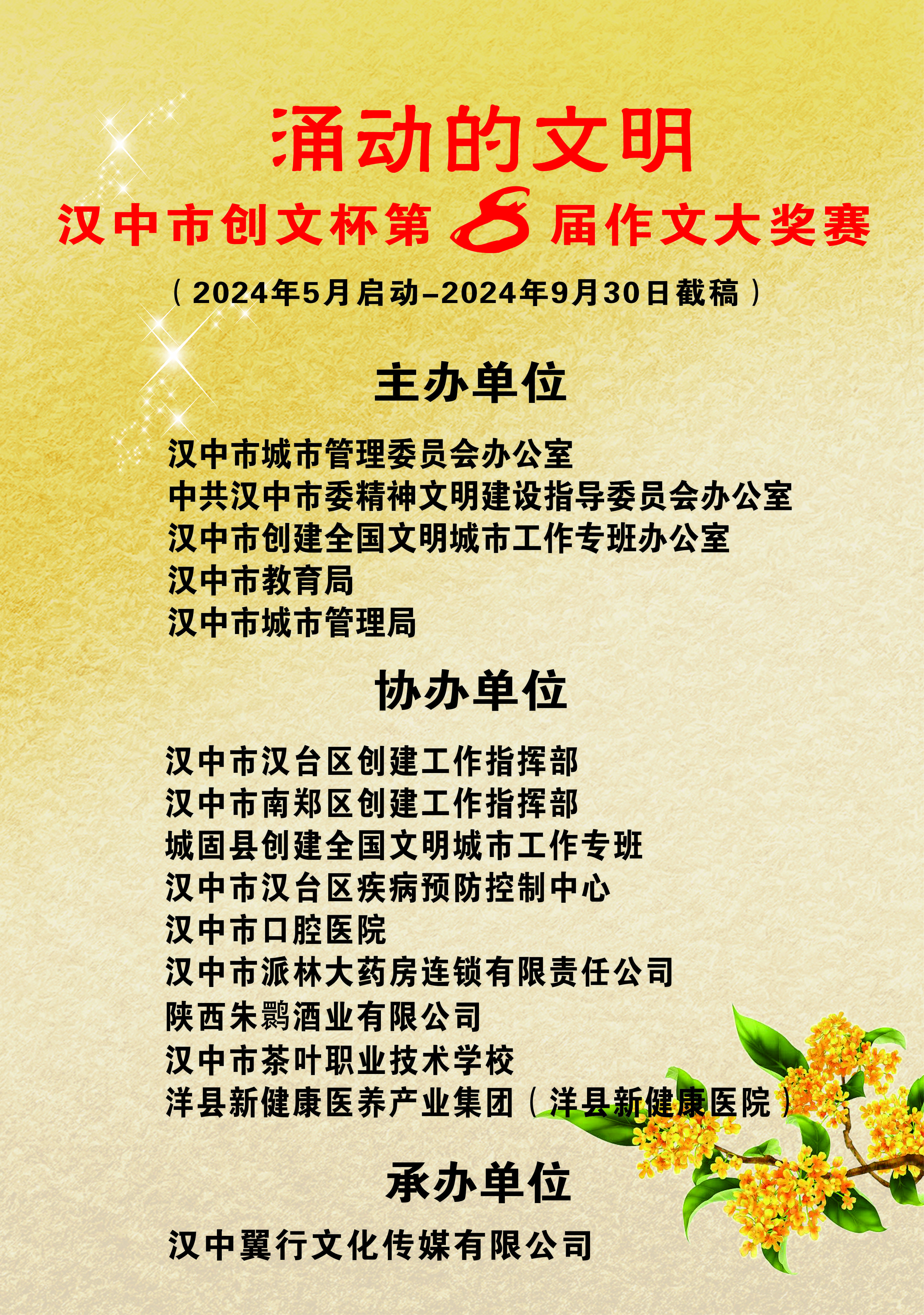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
——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第三章)
刘 诚
概念的提出:对神性写作的初次界定
在老子哲学中,宇宙由两个相反的部分构成,第三者从来就没有出场 人与世界同构;除了生理层面的男性和女性,在精神层面也由两部分构成,就是兽性和神性。由这两部分构成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人性,符合人性的本意,就好比人的直立,离开了哪一条腿的支撑,都没有办法真正成功。神性为阳,兽性为阴;神性为光明,是向上的,有光明正大的特点,兽性为黑暗、盲目,有下坠和堕落的特点;神性为理性、为灵魂,是空灵和飞动的,自律的,内省的,逃离的,形而上的,兽性为欲望、为本能,是放纵的,崩溃的,垮掉的,盲目性和创造力并存,如决堤的洪水不择地而出、不择地而流。由于兽性的存在,人间才是热的,现实的,有推动力的,生机勃勃的,但也正由于兽性的存在,人类永远不可能脱离大地的苦难——这两性都不可或缺,少了哪一块,人就不再是人了。可是这两个部分并不是平起平坐,正如《易经》里的“乾”和“坤”——“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这里包含的是创造的法则,创造是什么东西?就是原来不存在,使它存在;人性中的神性在这一点上是和宇宙构成的原理相通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元”则包含了实践和终成的原则,万物皆赖“坤元”而生,生就内涵着其后的成。“坤元”被“乾元”包容,有所成,才能使“乾元”不落空,不陷于虚无,正如人性有兽性,才有实体,神性才得以有所附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成为灵魂的现实。“坤元”不能先于“乾元”,因为它受“乾元”创造原则的领导,要是先于创造原则,一定迷失方向。没有方向理性作领导,只有技术理性,这个社会一定会迷失方向,正如人性如果只有兽性,没有神性,必然完全盲目⒃。在人性的复杂构成中,神性处在领导的地位,一旦离开神性的牵制,人性一面肯定要向下,将人性整个拉向兽性的深渊。兽性和神性都具备的人性,才是完整的不可让渡的灵魂,才有好戏可唱。一个人欲极端膨胀的世界,就是兽性极端膨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但谁都可以出来充权威,每一个只猴子都可以穿上衣服,执意要与神平起平坐,而且没有法官,人与世界的对立势必达到极限。这是一个由大写的人主宰的世界,在这个天国里将只有人的叫嚣,却没有天使,也没有神,在这里人自己就是上帝(将神性完全剥离、抽空以后的人性,就是这样一种沐猴而冠的东西。在一个个人权力意志极度膨胀的世界里,在一个个人主义、极端利己主义,一个以个人欲望为惟一最高律令、以肉体快感为惟一追求目标、各种居心险恶的“主义”在时髦辞令包装下轮番登场的时代里,你可不要指望人性会忽然变好)。这样一个只强调兽性一面的人性,只能是畸形的人性,是迷失方向的人性,连跛神也不是,只能在原地自我毁灭。这样一个只剩下各种“意志”的“作为意志表相的世界”,也是使叔本华悲观的根本原因;这样一个被肆意涂改、面目全非的尼采超人,也正是人性放弃神性而恶性畸变的典型个案。神性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出台,它是应着时代的召唤而来;它不是重新出场,而是被重新命名,重新受到重视。那么什么是神性,什么又是神性写作?在高难度的诗歌创造领域,神性与写作是怎样的关系?
什么是神性写作 什么是神性?或者,什么不是神性写作,而什么就是?先说什么不是。在我看来,凡只知肉体,只在生活平面以下的黑暗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不是神性;凡只见物不见人,只见人不见神、只见肉,不见灵,只见肉体快感,不讲永恒的,不是神性;凡只见垃圾、只见阴暗、不见神性光辉,凡看见了神性的光辉、却心怀仇恨、永远不能抵达神性世界之光亮边缘的,不是神性;凡拉时代向下、或试图拉人类同归于尽的,是文学的恐怖主义,不是神性;凡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只有狂妄、没有敬畏,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不是神性;凡企图唱衰神性、欲将神性从人性中完全逐出、任由兽性一性独大、一性独尊的不是神性;凡不能在尘世之外取得第二视角、与上帝的眼光格格不入的写作,不是神性写作;凡阴暗、绝望、用形形色色的时髦理由,将文艺对时代、社会和人类的责任强行推脱卸载的,不是神性;凡自绝于神、切断与神的全部联系、在一条与神相反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写作,不是神性写作。神性意味着出离和得救,凡不得救、或拒绝得救、也阻绝别人得救者不是神性,而反之则是。在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诗歌里全面破产之际,我相信只有神性写作出来收拾残局,使重建中国诗歌的稀世辉煌成为可能。
神性不是对人性的否定,而是人性中最高尚、最通神、最接近神的位置、并放射光辉的那个部分是人之为人、人之距离兽性最远的那个部分。在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人生舞台的每一个领域,人性中的神性一面都有出色表现。正是由于神性的存在,人性才不盲目,永不被欲望的下坠力量毁掉,并对这种下坠的力量保持警惕;也才是美的,在内忧外患的艰难时世里,人类经由神性为自己保留了得救的可能。神性写作,就是重新回到神性,承认神性好,比人性优越,就是让写作向神性靠拢,就像飞蛾向火靠拢、铁屑向磁铁靠拢。神性不等于神,只是神的精神和品质在人性内部的派定,也不代表一种方位,或对某种题材的特别强调,只要有神性在,写什么都会有神性闪闪发光。神性不是技术层面的东西。神性是一种弥漫和笼罩,是绝对理念横跨万有的美丽游走,而神性写作则是诗对于神性的固定和捉住,目的是证明神性在人性里的存在和它的绝对优越。
神性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神性写作是神性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保持了向上的方向,在当代中国混乱的诗歌现场为诗歌保持了趣味的纯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西川、王家新、黄灿然、臧棣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诗人,是当代中国自朦胧诗和海子以来最有价值写作的一支,而且本身也是神性的,可是他们仍然不能正确反映神性写作的全貌。知识分子写作有一种正气和清气,味道很正,可是书卷气太过浓重,是诗歌里的林黛玉,而不是诗歌里的二郎神、李天王、七十二星宿、更不是诗歌里的上帝。在知识分子诗歌里,我们找到了诗歌作为精神贵族艺术的全部精细和精致,甚至找到了与西方古典艺术非常相似的典雅的气质,却没有时代的鲜活、时代生活排空而来的盛大气象及其异质和浑浊,没有当代中国社会进程多声部的交错混响和当代中国生活的原汁原味;只有神性写作的清正纯洁,却没有神性写作的尖锐和雷霆万钧的强大威力,实在是力道不够。不如神性写作之神龙在天、天马行空,不如天上大神之威而不怒、灵动飘逸、潇洒风流。知识分子写作只是向神性的献媚,只是将脸朝向了神性,而神性写作却要求与神共舞,与天上的大神齐名,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上与神并驾齐驱!知识分子是神性写作的一种病态样式。神性写作是给知识分子写作注入更多的阳光和当代血肉,是神性在当代诗歌写作领域里的全面焕发!
神性写作与回归写作 回归写作是我在当代诗歌现场看到的另一种神性写作,但是它也不能够反映神性写作的全貌。回归是平面的,是两极世界里一次从一极向另一极的运动,在诗歌的当代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神性写作要求向上,是另一个向度的诗歌起义和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现场开辟第三极的伟大行动。回归的提法,有与神性距离最近的柔和、圆润,有神性世界所固有的古典韵味,却不足以表达神性写作的锋芒锐利和咄咄逼人!缺少神性写作的自由挥洒、神鬼莫测和飞扬妖冶!回归在根本上与神性写作相通,可是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诗歌艺术上的保守,从而给一些不思进取的诗歌门外汉留下浑水摸鱼的机会,也容易给一些人攻击神性写作留下口实。我曾经大力鼓励过回归的倾向,可是我发现,真正能够让我个人完全心仪的还是神性写作,神性写作包容了回归,但比回归写作的位置更高、更丰富、更多姿多彩,是回归写作的一个大解放、大升华,更逼近诗歌艺术的本质。回归诗人群中那些杰出的诗人并不需要艰难的角色转换,只要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写作其实是神性写作,就可以是神性写作,甚至可以比一般的神性写作诗人更好、更出彩!
神性写作与英雄写作 英雄写作是批评界对此前我个人诗歌写作的命名,同时也指代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堪与非非主义、他们诗派、知识分子写作并驾齐驱的第四大写作倾向,其代表性作品为我出版于二零零二年的诗集《愤怒》,这部诗集收入5000余行系列长诗《命运·九歌》及一大批短诗作品,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铁证,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诗人同行的关注和认可。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神性写作与英雄写作的不同。英雄写作是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并在那里滞留;神性写作却是照耀和启示。英雄写作是要绑时代大恶到众神面前对质,因此也是一种抵达惊人深度的写作,而神性写作却是对恶的劝退、宽恕、怜悯,是视恶为极端下贱,为残缺、为极端丑陋、为彻底失败,是不把恶当恶,从自己的世界里完全逐出和屏蔽。英雄写作是近距离的肉搏、白刃战,是与时代大恶的相朴、一对一的角斗、或一对多的生死格斗、是货真价实的擒拿格斗、是拼刺刀;神性写作却是从善与恶白炽化的战场上突然抽身而去,让时代之恶如坠五里雾中,笨头笨脑找不着北;英雄写作是战役,而神性写作是战略的安排,是重新划分世界的宏大构想。英雄写作是战士的写作,过多地强调了对敌人的恨,对人间的爱却强调得不够,尤其是包括对敌人的爱,对敌人的宽恕和悲悯,刚性有余而温软不足;太多金刚怒目,而神性写作却是面对恶的充分优越、对恶的宽恕和悲悯,不仅意味着提法的改变,而且意味着境界的放大和提升。从英雄写作到神性写作,说明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内在生命的品质上,我都做大了。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长达二十年时间的英雄写作时段里,我总是幻想着单兵突出,试图像特种部队作战一样,凭智慧和勇敢快速穿插、穿过恶的密林,然而每每深陷其中;同时由于我没有对整体的恶作出恰当的安排,因而只能年复一年地在与恶近距离的周旋中疲于奔命,击毙了一两个具体的恶,却放过了更多的恶,而恶真是太多、太多了,他们潮水一样一齐朝我涌来(这里面就有不少诗人同行),以致给恶留下了过多的破绽,给恶留下了太多的机会,永远不能将战场清理干净(神并且嘲笑我说:除恶务尽只是幻想,善有生的权利,恶也有生的权利,恶就是善的影子,通常同时出场,且将善紧紧追随),现在我通过神性写作将这一切中止。神性写作将实现对于诗歌领空的绝对控制,因为空权至上,控制了诗歌的领空,也就控制了诗歌的世界,包括海洋。神性写作不是受到谁的启示,而是英雄写作的自动生长,是英雄写作的成年,是神性在英雄写作里的自动觉醒。神性写作是对英雄写作的继承和发展,自然延伸和升华,经过了英雄写作二十年的历炼,一座座诗歌的城市被我占领了,一条条诗歌的道路修好了,一座座诗歌的机场已经抢占到手,神性写作的航天器该起飞了。神性写作就是把英雄写作中与恶直接抢白和对话的荣誉收回,让恶再也听不到诗歌说什么,让写作构成恶的灭顶之灾,类似最后的判决,因而从整体上对神性感到害怕。在英雄写作那里,因为零距离对峙,恶还有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侥幸取胜,有时则是平分秋色,在神性写作这里,任何恶都不可能再有任何机会,神性将恶完全排除,隔绝在神性以下。在中国当代诗歌里,最逼近神性写作境界的也许当数海子,但海子自有海子的问题,神性写作越过海子,将特别强调情绪的节约和控制,更讲究战法,不准备重蹈海子覆辙,自己摧毁自己,迫使神性写作的伟大事业毁于一旦,功败垂成!
神性写作就是以神性为惟一背景的写作 也就是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但肯定比这个更大。提出神性写作的策略考量是:为诗歌划分世界。神性写作不是对诗歌题材的强行规定,而是对于诗歌题材边界的全面超越,是神性在所有题材上的沉思与游走,和对所有题材的诗性处理。并不是你只写月亮、星星、天体、云朵及其神的故事,你就是神性写作,恰恰相反,你写了很多星星、月亮,也写了很多的神,也可能完全没有神性。神性不拒绝人类世界的一切事物,只要诗人本身是神性的,则写什么,也可以神性飞扬,闪闪生光!一个在中国诗歌里浸淫多年,却没有看到诗歌的这种向上与向下之争的根本命题的人,在看穿了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套写作阴谋之后,他立马就会在神性写作的大旗下重新站队!一个不知道诗歌为何物的人,由于神性的突然觉醒,也可以在一次午间小睡之后,开始向一个神性写作优秀诗人的目标单兵突进!一个后现代主义诗人只要神性觉醒,放下解构的屠刀,也马上就可以迈进神性写作的门槛,神性写作的大门为所有的诗人敞开!它属于一切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也笼罩一切诗的流派!它的空间很大,比能够想象的还要更大,更辽阔!可以容纳众多的诗歌流派!可以容纳得下当代任何面向极限的眺望!神性写作将中国诗歌分为阴阳两界,正邪两界,善恶两界,而将其他言不及义的划分统统取消!神性写作是诗歌里的宗教!是后现代主义废墟上空人类精神理性的最后殿堂,有着天堂的全部外观!而只是在神性写作百万座神庙的某一个分殿里,才写着这样的字样:反后现代主义。
超越的激情:对神性写作的近距离描述
诗到神性为止,神性以外没有诗歌 也许渺小的诗歌可以不要神性,仅仅有人性就可以了,甚至连人性也可以不要,只要流氓性和痞子性就可以了,可是所有伟大的诗歌都必须是神性的,必须像天上的大神,以光明磊落的姿态,统领起生活里所有的正面力量。也许屈服于市场,以向市场献媚、以取悦于市场、并以此取悦于时代的诗歌可以不要神性,仅仅有性、有垃圾、仅仅有劣质读者的掌声及一些劣质诗歌从业者的追随就够了,而一切伟大的诗歌和企望向伟大逼近的诗歌,都必须沾带着神性的灵光,至少必须通神,必须在诗歌的每一章节、每一个修辞的容发之隙,为神性留下一个必要的位置。也许以加速人类更快地毁灭、借以快速成名、以便从当代名利的轮盘赌里抢到更多好处的诗歌写作可以不要神性,甚至可以反神性,比如我们看到的那些以解构的小技巧写作的小情景诗、小情趣、小调皮话诗、正话反说诗、恶作剧诗就是这样,而真正见证一个时代、试图为一个时代命名的主流诗歌写作却必须有神性,没有神性的存在,诗歌将光芒尽失,只能传达地狱的声音,在地狱的高度以下潜行,永远不能获得光芒和力量,以天堂的歌唱照亮世界使苦海骚动。
艺术必须准备对时代负责 艺术对时代负责,首先对自己负责。神性写作不承认人类为天之骄子,拥有法外特权。虽然无法确定一百年后的艺术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那些曾经在艺术史上导致一大批煌煌巨著产生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永恒真理不可能在后现代到来之后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忽然改变。艺术仍将诉诸人的心灵,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现代艺术家不是下贱地跟在那些心怀鬼胎的所谓先锋艺术家后面瞎起哄,不是跟在那些靠运动吃饭的伪艺术家后面不停地操作出一些走马灯一样的艺术流派,在现代的条件下,吸收一切现代艺术的有益成分,重建真正艺术的古老尊严和稀世辉煌是完全可能的。我们不缺少才华和精神的能量,只缺少一个必具要件,就是彻底放弃对新和洋的盲目崇拜,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信赖、也值得我们永远信赖的。当我们将伪价值的东西剥离、抛弃,那些与根相连的部分,正在显露出它们峥嵘的真相,它们甚至依然美丽、鲜活如初!这意味着中国当代诗学必将经历一次重要的变化,意味着中国诗人主体人格的觉醒和困境里的坚守。我们相信中国当代诗歌,必将在中国血与火的生活进程中产生,有所作为。它是继承了中外两大传统之中一切优点的,而不是食古不化、或无父无母的;它是中国作风、中国做派的,而不是食洋不化、怪腔怪调的;它是取材于中国这片土壤的,以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丰厚生活为血肉的,而不是凭空而来的天外之物。中国诗人的思想资源和灵感,只能从现实的中国社会进程来,不可能从外国来,国外并不存在一个汉语诗歌的天堂。很显然,这里尖锐对立、而又相互缠结、咬噬、强劲涌动的生活,既产生思想,也产生诗歌。那种神性的、有金属硬度和质感,可以点燃灵魂的美丽诗歌,一经出现,全世界仍将为之鸦雀无声!
对街痞和淫棍而言,有比诗歌更好的去处 对于这些人来说,诗歌从来都不是一个可爱的事业。尽管在每一个朝代,因羡慕诗歌的光荣、因而比谁都起劲地挤进诗歌现场的人永远不在少数,可是他们最终发现,这里只是真诗人修行的地方,诗歌作为一个危险的行当,也许正处在炼狱之火熊熊燃烧的中心;对于没有准备的人,误入诗歌歧途甚至是危险的,本行当最大的风险在于:它很可能弄到后来,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既没有得到诗歌,又白白断送了黑帮老大的黄金前程。诗歌是精神的耶苏,诗歌的写作是一种代人类赎罪的行为,使它更多与苦难的承当连在一起,这样的高难度,将吓退诗歌门前所有犹豫不决的身影。我们从来没有发现一个连人也做不好的人,居然能够胜任诗人的高难度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对诗歌也永远不失掉信心:每当诗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时候,总有一种相反的力量从诗歌的内部产生出来,推动诗歌自救。向哪里走?向上走,向神性的一面走,舍此别无他途。诗歌可能因为在高处呆得太久,有时会有意降低姿态,去倾听人的卑微的求告,替他们将心中的苦说出,可是它的位置不在那里。诗仍然是神性的东西;你可以将神从人间的生活里放逐,但你必须在心里为神性留下一块不需要很大的位置,这个位置是永远有效的,确保不被任何私心的算计给挤占的,任何的挤占,都将直接造成诗的隔绝和缺如。
当前诗歌写作的所有问题都是将诗歌的头颅强行按低的结果 当前诗歌的所有困惑,都是在兽性写作与神性写作之间的困惑;当前诗歌写作的所有对立,都是兽性写作与神性写作的对立。将诗歌的头颅强行按低,曾经是诗人争取的权利,结果人们已经看到。中国诗歌如果能有一个辉煌的世纪,这个世纪只能由神性写作创造。神性写作是侧重于神性一面的写作,不是要取消兽性——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取消兽性,或者在兽性与神性的对立之中平分秋色,找到平衡,而是要承认神性一面的绝对领导地位,它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惊世骇俗的伟大诗歌诞生。不是要俗化,而是要圣化;不是要崇低,而是要崇高;不是要作低诗歌运动,而是要作高诗歌运动,要在一个比生活平面高很多的高度上飞行。诗歌要有光芒,这光只能从神性来。完全没有神性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没有亮光的世界。神性是对于人性的深度开掘;神性不是天外之物,就在人性的深处。神性是人性的灯塔,是人性里最光亮和辉煌的部分,但也最脆弱,最容易被吹灭,吹灭了,人性的黑屋子里就只有黑暗,而一旦神性的风吹过,所有的事物都将呈现出诗性的一面,重又变得生机勃勃。当神性的手触抚摸了没有生气的语言,语言立马活泛起来,焕发出诗的灵光。神性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预留在人性中的东西,你可以遗忘它、埋没它,不让它发光,却不能把它取缔。但尽管遭到了遗忘和埋没,当神性的诗歌出现,它将被重新激活。诗歌要有热,只能从神性来,因为只有神性一面,才真正关心人,从根本上关心人,不仅关心它的现在,更关心他的将来;既关心他的快感,也关心他的根本福祉。只有神性的一面,才能确保诗人在任何时候都分清善恶、是非、真假、美丑。诗歌要有庄严感,庄严感只能从神性来。诗歌要有深邃的境界、惊人的句子、复杂和高贵的调性,只能从神性来。如果在过去的诗歌阅读中,我们曾经找到了惊奇,那完全是对于神性的惊奇。神性是一种回天再造的力量,使人和诗歌变得美丽。神性可以把特丽莎修女从一个平凡的女人造就为圣徒⒄,也完全能把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造成杰出的诗人。因此,当我在这里说:从现在开始,在中国诗歌的现场重建一种神性写作,并不是跟你们说说玩的,它是当真的,这个过程很可能已经开始。我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写下这样的宣言,而且能够写下这样的诗歌作品——我有两手,两手都很硬。我愿意在我的诗歌旗帜上写下“代神立言”四字;而且,我十分欣喜地看到,更多的人们将认可这样的写作。我相信,当诗歌重新意识到自己“代神立言”的职责,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将从此黯然终结。
说人话与说神话 后现代主义诗人说,要说“人话”,而不要说“神话”。并声称他们的诗歌决不说“神话”,好像说“神话”是一件可羞和可耻的事。这话其实只对了一半。神当然不会开口说话,可是神会暗示。在每一次感性事件的下面,都为进入事物本质保留着最便捷的通道。说“人话”并不影响我们让“人话”带上神性的灵光。神性将为我们的“人话”加冕,使它深刻,中庸和大,合法度,使它奇崛,立于不败之地。说“人话”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神话”的从骨头里的羡慕,也丝毫不会影响到一个上等人在任何时候对于神性的仰望姿态!你们的意思大概不至于说,所有与神沾边的东西都是倒霉的东西吧?说“人话”,人爱听,只说让人高兴的话,让人感到入情入理的话,说常情常事常态,这样的诗歌态度固然平易,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拉拉家常,也不会让人感到压抑和自卑,你巴结他,说出了让他产生“快感”的话,他听着顺耳,心里舒服,让他感到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人格上,他都可以和一个诗人平起平坐,甚至看起来站得比一个诗人还要更高,这样的诗歌可能赢得市场,却与人类的根本利益无益。你不过是在哄骗(其实也是在贿赂)读者。而最终,你只能让一部分读者满意,却不能让更多的读者满意,高品位的读者会感到甜腻和肉麻,未来的人们更不答应。你只能让读者产生“快感”,却不能让读者震惊,感到敬畏。神性写作的观点是:如果你坚持要说“人话”,这也不错,但是你一定要为神性留下必要的通道。你说“人话”,但是还必须准备说“神话”。说“神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你说“神话”,但是同时不拒绝说“人话”,只是为了把“人话”说得更好;二是你要准备说“神话”,并且知道什么是“神话”;三是你必须说得好,不能歪曲了神的原意。你说的这些“神话”是给人听的,不是给神听的,但必须得到了神的允准,与神的旨趣和精神相通,从神的一面看是满意的、可以被认可的,否则就不是神性写作。
神性写作从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从来没有中断 老子是。庄子是。孔孟是。司马迁是。屈原是。李白是。杜甫是。曹雪芹是。朦胧诗写作是。昌耀是。海子是。英雄写作是。知识分子写作和回归写作是,虽然它们强度还远远不够。神性写作已经形成了伟大的传统,被中断了的不是神性写作,而是反神性写作。这些反神性写作,有许多流派,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否认人性中有神性,甚至仇视神性,视神性为妨碍、为肉中的毒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他们拉人性下水,诱骗它走向极端,把它推向空前高大的位置,推动人性更快、更快地朝向神性相反的方向——即兽性的方向滑行。最后这个世界就剩下一个无法无天、对一切美好情操都嗤之以鼻、对一切权威和律令都拒不承认、也拒不听从的人!就剩下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对世界这也不顺眼、那也不舒心,惟独不反对自己的极端自私的动物人!就剩下为了写作的渺小目的,即使拉人类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的诗歌怪物!这实际是对人本来可以达到神界的伟大潜力的盲无所知和粗暴毁弃。
神性写作的实质是对神的敬畏 神性写作并不认为人,可以按自己意愿无限改变世界的结构,也不承认人有这样的特权和能力。我们接过的这个世界,决不是一种事实的零乱堆积,而是某种神迹,诗歌只是世界固有的性质,在上帝造物的时候与世界一次成型。诗和世界是不能分开的。诗只能显现,只能指证,却不能据有或拿走,诗是世界自己的。诗人并不能创造诗歌,诗歌自古以来,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也不会被诗人的写作穷尽,诗歌还是诗歌,它在世界那里。诗人自以为创造了诗歌,那只是假相。诗人以为诗歌在自己心里,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从怀里抽出万卷诗行,那也是假相。诗只是在它自己高兴的时候,偶然把它的投影倒映在诗人的心里,而且必须是一颗没有被污染的心才行,它的水是清澈的,而且很快又把这投影收走了。罗丹说,美是发现。诗就隐藏在事物之中,只有神性不灭的人才有更多的机会看见。他走到哪里,诗歌就显现在哪里;他向哪里看过去,诗歌就在哪里出现。包括语言,也为着这神迹而来。它因为刚好能够表达神迹而被视为神圣,如果没有作为神迹的存在作背景,语言没有任何意义。在字典词典上的字,它只是一堆杂乱的字,此外什么也不是。在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语言为我们保留了与诗歌对接的接口。所谓一首诗的写作,当是指潜藏的神性,刚好走过了语言的桥梁。神性写作就是与全人类的价值系统全面接轨。价值系统乃由神创,是神对人存在的一种万世不易的预先设定。神性写作就是让真回到诗中,让善回到诗中,让美回到诗中。就是让博大、宽厚的道德感回到诗中,让真善美在诗歌里合一。
神性写作,就是承认人性的缺陷,直面人性贱的一面、丑陋的一面 人性不如神性,因为人受欲望指使,是欲望的人质。神性写作就是承认人性的缺点,承认人性的盲目、不自由和苦,不为人性的缺陷而讳,同意给人性加上必要的限制。神性写作认为,纯粹的人性很丑,几乎等于兽性,如果不加以修炼,是绝不可以成圣的。最好的人性,顶多只是一毛坯,不能发光,也不可能自动成为好的器物。成器的过程,就是将它的杂质剔除,将多余的部分剥离,为它赋予必要的形状。对于一般的人,成圣的道路布满了荆棘,也太过遥远,且于人在当世的功名利禄不会有任何好处,他们拒绝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可是身为诗人,为什么要拒绝呢?有一次成圣的机会,难道不是很好!在诗歌的历史上有过许多诗人,企图在诗里用兽性置换神性,可是他们都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他们的诗也失败了。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最好的诗歌,都不是将神性放逐以后产生的。我们所找到的最好的句子,都是神性写作的句子。我们找到了那些足以点燃和照亮灵魂的东西——乃是中外诗歌里万世不易一颗神性的光芒四射的神圣内核,乃诗心!只有这样一颗伟大的心,才能使我们与诗歌的纯粹保持同一;并使我们因了自己的努力,在人类历史的又一个重要关头力挽狂澜,促进人类得救,最终使自己得救,并使自己得以避免见证现代艺术沦落的惨烈黄昏。
神性写作三指标:向上、有益、尖锐
向上 这是神性写作在文学坐标上的根本指向,就像指南针一样,神性写作的价值指针将始终指向天空。它不能用平面的思维把握,只能用立体的思维把握。神性写作准备把地面留给后现代主义,而自己向上。那里是什么?天空!我提请诸位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一片伟大的所在!那里,无数奇迹所在的地方!那里龙和神的舞台,宇宙的多变的面部,清清一色,你却看不透它!那里有多少星体在闪闪发光,而白天你却看不见它,只有在晴朗的夜晚,才能与它们漂泊而来的一缕神光相遇!那里有成片的几千万亩的云朵缓慢移动!那里下雨,行走日月!那里风云集会,可以容纳亿万人群眺望的极限!一大片新大陆一样的所在,就在我们的头顶上空,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诗歌的陆军前去占领?而这正是神性写作所要做的!神性写作准备与地上的存在至少在十到二十年之内拉开距离!神性写作效法昆鹏,神性诗歌只与天上的大神齐名,并肩!从英雄写作,再到神性写作,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回答!也是我对诗歌的回答!为什么要向下?向下本来不难,难的只在向上。地球上的物体,自己就有向下的力量,因为有地心的引力在。向下人人都会,向上却需要作功,伴有能量的消耗,意味着对困难的克服。向上意味着对平庸状态的叛离,意味着高难度的动作,意味着在没有梯子的情况下攀登青天。向上,意味着一种对于高度的需要,自从创世以后,上帝就从那个方位看宇宙,始终一语不发。向上,就是要取得尘世之外、乃至宇宙之外的第二眼光。如果真正要比向下,我建议看看谁能够下得最低,到地层以下,到几百公里的深处,那里岩浆奔流,能在那里体会一下地球心脏的热度,也未尝不是一桩英雄的壮举——我是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也就通向了神性,可是千万不要只在“下半身”那里停下,也不要在“垃圾”那里停下,永远不与生活取一个平面,不和生活里最没有希望的那一个层面呆在一起,甚至眉来眼去,打成一片,更不要与生活里的浊流同流合污。让诗成为一种净化的力量;让诗成为与人间对照的世界,成为照耀人间的第二重天。向上意味着飞动;向上,却永不脱离对人间的关爱,仍然看着它,以神的无比明晰和透彻的语言与它交谈,引领它保持住那些该保持的。向上,因为光来自空中,再返回空中,诗歌的非凡的大幸福、大欢乐在空中,所有飞行的翅膀在空中。神性写作与人间拉开了距离,但它并不离开,因为它最终属于人间,它的锚就留在那里——存在之海的深处。
有益 诗歌可能有一千种标准,一千种标准都对,各有道理,可是神性写作在这里只强调“有益”这样一个标准。这是一个简单的指标,也是最低的指标,也是最好用的指标。诗歌写作在当代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它们都必须是有益的,即有益于当世,有益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持续生活。所有的神性写作都是有益的,是与人类价值完全接轨的,它不是断裂的,因为有这个接轨而与全人类息息相通。诗歌不可能救世,但必须确保不使自己有害,在复杂的当代条件下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神性写作强调道德感——诗歌不等于道德,但必得有道德,道德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从神性写作的字里行间透出,就像气体将空间充满,你却看不到它,有时还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你只是在危急的时候才感觉到对它的需要,可是它已经在那里。道德在神性写作这里不是空置的,是神性写作的先在条件。神性的诗歌,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写作的有道德精神支持的硬朗的诗歌,光明正大、可登大雅之堂的诗歌。神性写作不是要在人间恢复神的统治,而是要强调神性在人性这片土地上对兽性的绝对领导地位,把诗歌从精神暴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欲望的人质状态下解放出来,使它自由、健康和富有生机。神性写作不是一个流派,但是倡导一种有益的共同倾向。神性写作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将高贵的艺术创造纳入人类在这个美丽星球永续发展的宏大背景,力争成为这个背景的一部分。神性写作决定让真回来,让善回来,让诗歌有益,成为一种有益于人类的特殊知识。同时让美回来,让崇高回来;让上帝回来,让神圣的事物回来,在诗歌里全面重建对于神圣事物的绝对敬畏。神性写作准备让比赛在价值的平台上继续,因为有价值判断的比赛是美丽的,可信赖的,能在这场比赛里获胜是光荣的,因为有价值评判的比赛规则大方向绝对正确,比赛指向的地方是诗歌最高级别的荣耀。能继续这场比赛,表明我们没有因为私心而逃避,也没有因为胆怯而退却,甚至是一种神圣权利的象征,因为只有那些有准备、有德行的好人才得到了特殊的召唤。神性写作不认为一个生活的忤逆子真的能够在真理的道路上走到很远,并且不认为这样的忤逆子果然会有多大的才华和能量,真的能够拉人类一起同归于尽。神性写作决定让诗歌成为拯救的力量,令所有恶势力胆寒的力量。神性写作决定向诗歌里一切正直力量倡议,大家都起来为反后现代主义的美丽事业添砖加瓦,有力出力有智出智有才出才有钱出钱,神性写作决定在诗歌里来一次大扫除,将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生硬语词从诗歌里清除出去,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诗学观念从最显赫的位置上全都清除出去,连同它们的毒素;神性写作准备心情愉快地为中国后现代主义在棺材盖上敲上最后一颗钉子,以便拯救世界,首先拯救被后现代主义劫为人质的一代中华民族新人。神性写作是异端的异端,对破坏的破坏,对否定的否定。神性写作的口号是:从生到死,永远不为快感写作,不为任何时髦的主义写作,也不为任何鸟人的眼色写作,仅仅为绝对真理写作,为永恒的生命写作;并且为生活里永恒的爱写作,为人类惟一家园——永恒的自然写作,为支持人类站立于天地间的不朽信念写作。为人类从古到今一切美好的情操写作!写作一切的美好,从而使写作美好,并使写作的人美好!如果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一点美好,神性写作准备让它至少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保有一种美好——这就是写作。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神性写作的具体步骤是:先做人,再做诗,做很多很多的好诗,做很多很多有分量、能传世的大诗,然后——成圣。
尖锐 尖锐包括了新和锐。神性写作正是在这里不满于知识分子写作和回归写作,因为他们没有神性写作必不可少的尖锐和强度。但我不想用“先锋”二字来对神性写作作出描述,因为这两个字被伪先锋们盗走,用作欺世盗名的专利产品已经很久了。他们并不了解这两个字,可是霸占了这两个字,强奸了这两个字,让人一听见这两个字,就头皮发麻非常恶心。神性写作准备让尖锐成为必要的状态。神性写作向存在发问,执意要击中存在的要害部位。神性写作认为,诗不单单是一个技巧问题。诗歌的力量来自诗人的人格,是诗人的人格使诗歌强大和有力。神性写作建议放弃纯诗的幻想。神性写作将不拒绝政治;神性写作有时站在时代的前面,有时站在本时代的反面,有时站在时代身旁五百码的地方,完全以时代与价值的关系调整方位和角度。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当代,——面对当代的乐,也面对当代的苦。神性写作认为当代是每一个诗人从命运那里领有的一份财产,当代是诗人灵感的源泉和写作资源的宝库,是诗人打磨诗歌宝剑的硎石,是诗人成圣的惟一平台,其炉膛的温度,恰与成就神性写作必不可少的要求相应。这份遗产的领有,将使你的写作成为有话要说的,而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将使你的诗歌与历史上任何其他世代的诗人区别开来。当代是诗歌发生的惟一现场,神性写作认为,任何对于当代的漠视,都只能造成对诗歌的损害,从而失掉诗歌发生之根和当代经验的原汁原味。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心灵,倾听心灵的召唤;强调重建诗人的人格力量,认为在诗歌里坐着的,只有诗人的灵魂,那是使一首诗所以震撼人心的根本原因,此外别无所有。正如我们在小说里找到命运,神性写作不在艺术里寻找语言,寻找语感,寻找其它好看的东西,却希望看到诗人强大而又与众不同的主体人格。尖锐必然要求新,但神性写作首先强调思想的新,思想的前卫,首先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永不以诗歌说谎,渺视一切将思想抽离以后的形式上的离经叛道,决定让诗作为一种有效的载体,表达诗人对于一个时代的预言、评价和忠告!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决定永远站在一个时代的弱势一边,确保艺术的冲击力携带着本时代的道义力量,从而达到最大,辐射到最远。新,同时又是充盈的。——我不说美,而说充盈。美这个字也已经被人们滥用,许多人不了解美,却在谈论美。充盈是一种饱满的状态。首先是诗的充盈、诗味的充盈,是诗人主体人格的充盈,是诗歌元素的丰沛与饱满,是诗歌感觉的自由与活泛——饱满而且圆润,鲜活欲滴。让诗在最自由的状态下,保存一个诗人的全部生命信息。充盈与干枯相反,与概念化相反。神性写作不写干瘪的诗、苍白的诗、矫情的诗和观念的诗,不为任何时髦的主义写作,不为特定的时代气氛写作。神性写作不准备让诗沦为寓言,而是要上升为寓言,但却成功地避免了寓言的笨拙和枯涩,显得率意天成,因为它里面充满了人性、人情的丰厚内涵。神性写作也准备在诗歌里保留意义,因为意义不是毒药。神性写作是飞动的,有足够张力的写作,既有直线和生硬的锐角,有几何体,也有更多的曲线;在神性写作里,将有更多晦暗不明的异质物质出场。神性写作力主诗是多棱的,有多个不同的侧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打量,经得起高智商的二次发现;是合声的,有多个不同的声部,可以经得起反复倾听。就像一块多棱的宝石,经得起来自每一个方向的反复打量;它是单纯的,清澈的,而你却看不透它。神性写作决意继承以往全部写作中一切有益的成分,并把它们向独创全力推进,为当代诗歌艺术增添一些全新的东西。
价值不需要复辟,只需要诗人重新面对
价值不需要复辟 周伦佑们很快看见,价值它本来就在那里。不在于反价值事业遭受了多少挫折,而在于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如果说这是一次在文化后宫里发动的政变,这个政变是失败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价值并不因为周伦佑们起劲地反对而满面羞愧地自动退场。价值作为一种历经生活几千万年积淀而形成的事物,具有超稳固的结构。价值其实就是神性,是文化中那些核心部分,是人类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人类有价值,可免遭迫害。价值存在的意义在于,即使是终究没有天堂可上,毕竟还可以确保有一个差强人意的人间,反之则只能自蹈绝境,最终是走投无路。事实上,反价值的工作很难做,起劲地反对的结果,只不过在特定的时段造成了某些混乱,而价值本身是不会失败的,这是价值本性使然。如果你看到价值失败了,一定是伪价值失败了,而真价值却完好无损。真价值的“复辟”甚至比反价值者出手还要快,还要有效,它以不变应万变,习惯于后发制人。作为后现代主义中国版本的非非主义及其变种的徒子徒孙们,其实内心很自卑,知道自己的反对完全是竹篮打水,他们其实是羡慕价值,只是后来在那里遭到了冷遇。事实上他们很难把反价值进行到底,反到金钱面前就停下了,反到性面前也停下了,反到空气、阳光和水面前也停下了,反到美味食物面前也停下了,只要有美味的食物,这些人一定比谁吃得都香,而且食量惊人,吃相难看。事实上,在完成了为中国后现代主义代言的反价值的神圣使命后,周伦佑很快人去楼空——他回到了“红色写作”,又回到价值(也许他死死抱定了价值,根本就没有离开),强调建设“走向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强调走向本土,深入当代,面对生存;并在《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力无效》一文中,对后现代主义表示了强烈的质疑。
价值在哪里 价值的确是在文化里,是文化里最核心的部分,可是文化它只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也没有藏身在语言里,语言比文化还要表相。周伦佑自以为找到了价值的藏身之所,其实并没有找准。他看到他的敌人一闪身走了进去,可是并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根本下落。人类价值固然以语言作为物理外壳,它的根却并不在语言,而在人性的深处,被人类的祖先以秘密的语码写进了基因,植入了人性的黑土。人性不灭则价值不灭,人性——这才是价值的后宫所在!价值的后宫甚至与世界王者的后宫一样深,在同一个位置,而且完全重合!周伦佑们自以为身负时代重托,挺枪跃马冲到了文化的后院,要逼价值让座,可是他们注定不可能得逞。他们开列了一些词,试图从语言里清除一些字,可是留下了更多的字;他们开列了代表价值的词语黑名单,以为这样价值的家就可以给强行拆除了,可他们不知道价值虽然居住在词里,可它只是寄居,它的根并不在那里;即使侥幸成功,价值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重新为自己创造一套语言系统。价值是人性里的东西,就是人性里那个叫作“神性”的部分,亦即是与兽性相对的那个部分,要反价值,除非重置人性,甚至意味着重置世界的性质,而这显然很难办到。所以我在这里宣布:反价值不过是一次超级做秀,一次后现代主义坏小子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胡闹。价值甚至不必要出场进行回答,因为周伦佑们根本达不到价值所在的高度,以及它的广度。价值是大尺度的事物。坦白说来,我有时候真为周伦佑感到难过——不知看着早年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章,中年周伦佑是不是曾经感到脸红?
占有价值首先是为了诗歌自己 说来你们可能不信,天下所有自以为是的文化人、各类权威、名流、大家的所有的不朽事功,他们虽然顶着一颗权威的头颅,却都必须依靠价值背书,否则就不能生效。神性写作认为,诗歌不自外于人类主流进程,即使再怎样不济,可以没有诗歌,甚至一个时代也可以有诗歌的完全绝收,决不能让诗歌成为反人类、反生活的力量。即使有一千种理由,比如后现代主义这样的外国理由,诗人也没有权利让诗歌写作成为精神暴力的特别出口。诗歌必须爬升到价值的高度才有出路。一片价值虚无的废墟是没有办法建筑诗歌荣耀的,诗歌找到了价值,才是找到了生发之所和诗歌运动的目的之地,也才是获得了赖以立身于世界的不朽基石,任何诗歌的高层建筑都将因此而得以建立,不用担心因为没有可靠的基础而被轻易摇动。价值是生活的定海神针,是诗歌面向世界、取得定力的根本。与价值背离,将使我们的诗歌不被终极价值认同,被世界从根本上排斥。与价值保持同一,将使我们的诗歌最终成立,获得生命。价值使诗歌充实,因充实而成为有重量和有色泽的,就像秋天时候大地上丰盈饱满的果实,归于生活中劳动的人们。
————————————————————————————
注:本文系第三极神性写作奠基之作。全文6万字,2004年10月30日在网络首发,收入作者诗论集《先锋的幻想》,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于2004年11月出版,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