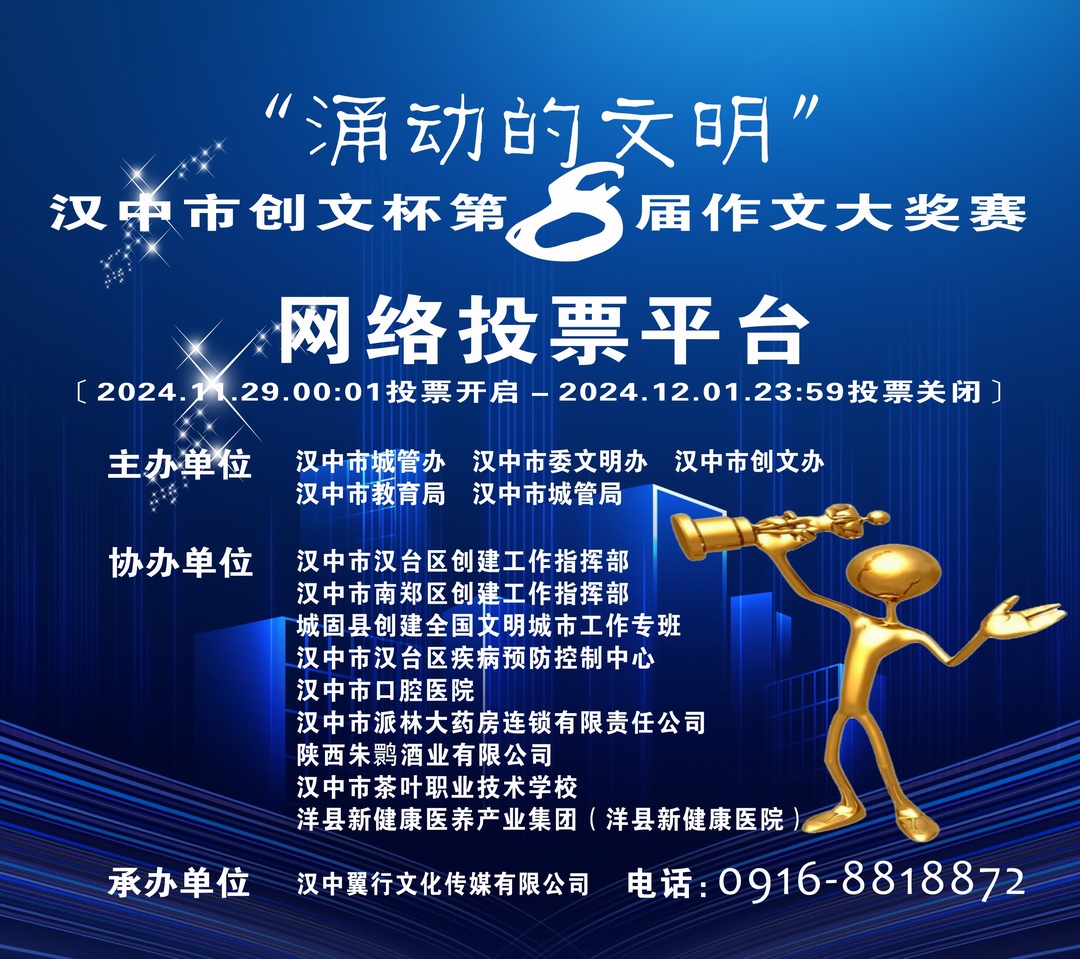托尔斯泰:写作有益的文学①
鲁迅临终前曾告诫子女:如果才华不足,就学一门手艺谋生,千万不要做一个空头文学家,为什么千万不做空头文学家?因为这样的文学家有百害而无一益。无独有偶,在列夫•托尔斯泰有关文艺的论述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只有当你有好的新的东西要说的时候,只有当那些东西对人们有益,对千百万劳动人民有益的时候,你才可以动手写作。”在一八五二年给哥哥的一封信里,作者写道:“我已动手写一部严肃的、我以为有益的小说,打算为了它使出我所有才力。我把这小说叫作一本书,因为我认为,人生一世哪怕写一本短短的,但却有益的书也于愿已足了……”同年,托尔斯泰在日记里写道:“毫无目的、不指望起作用的写作我坚决不干。”在一八五五年的一篇日记里又说:“看来,我已经被蓝色制服注意了,因为我的文章。不过,我希望,俄罗斯应有讲道义的作家;而要我做一个甜蜜蜜的作家可无论如何不干,同样,要我徒托空言,写些毫无思想、更无目的的文章,我也坚决不干。最初一刻气愤至极,我发誓不再拿笔了,再细细一想觉得,驾凌其他一切爱好和劳作之上的,我的主要的、惟一的事业应当是文学。我的目标便是文学上的荣誉。我可以用我的文章来达到善。”列夫•托尔斯泰不无狡黠地写道:“艺术——这种名叫艺术的人类特殊活动——跟人类其他任何活动有什么区别,这点我知道。但是,对人有用和有益的艺术作品跟对人无用和无益的艺术作品有什么区别呢?分界线在哪里呢?——这点我不能明确地说出来,虽然我知道,这条分界线是有的,有用和有益的艺术是存在的。”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迫使人们在永无穷尽、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中热爱生活。在致波波雷金的信中托尔斯泰又说:“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可以写一部小说,在其中我将无可争辩地奠定在人们看来对一切社会问题都不无正确的观点,那么,我不会花两个小时的劳动来写这部小说。但是,如果有人对我说,现在的小孩二十年后将读我写的东西,并且为之痛哭和欢笑并从而热爱生活,那么,我甘愿为这部小说献出自己的整个生命和毕生精力。”
这种坚定的信念,来自于作家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
“艺术,千百万人为之牺牲了劳动、生命,甚至道德的艺术究竟是什么?”列夫•托尔斯泰说:“像语言一样,艺术是一种交际手段,因而也是求取进步的手段,换言之,是人类向前进到完美的手段。语言使还活着的一代人可能知道前辈以及当代的优秀和进步人物凭经验和思索而得知的一切;艺术使眼前活着的一代人可能体验到前人所体验到、以及现代的优秀和进步人物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通过语言,人可以交流思想;通过各种艺术形象,人可以和其他的人,不仅当代人、也包括过去的人、未来的人交流感情。”他认为,艺术不可取代的功能在于,把破碎、松散的流沙一样的人类,在同样的感情中团结起来。他说:“由于人具有理解用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知道全人类在思想领域内为他做过的一切;他能够就在此时此刻凭借理解别人思想的能力而成为别人的活动的参与者,而且能够凭借这种能力把从别人那里汲取的和自己心里产生的思想传达给同辈和后辈;同样的,由于人具有通过艺术而为别人的感情所感染的能力,因此他就能够在感情领域内体会到人类在他以前所体验过的一切,能够体验同辈正在体验的感情和几千年前别人所体验过的感情,并且能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别人。”接着,托尔斯泰提出了成为艺术品的三个条件,即一,作者对事物的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二,叙述的明晰,或者说形式的美;三,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诚的爱憎感情,——这最后一条是最最重要的。在一八七八年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托尔斯泰写道:“说起来也实在是下作,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艺术领域里,只需要惟一的消极的品质——不撒谎。生活中撒谎固然下流,但还不至于毁掉生活;它玷污生活,但在其污秽之下终究不能掩盖生活真实,因为总会有人或苦痛地或欢乐地渴望着什么。但在艺术领域内的谎言却毁掉现象之间的一切联系,把一切弄得灰飞烟灭。”
这个时候的列夫•托尔斯泰,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不朽巨著,对于艺术的识见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从托尔斯泰不厌其烦的论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代文学巨匠对于后来人的忠告:写作于生活有益的文学,这应当成为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文学家共同信奉的最高原则;写作于生活有益的文学,将使得那个被叫作文学创作的工作变得严肃,充满了道德的力量和不能不为之献出一生宝贵精力的神圣理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壮丽事业的一种;写作于生活有益的文学,这是全部传统中最可宝贵、最值得称道的根本部分,它应当成为一个有良知的文学人内心的惟一永恒要求。正是因为有益,文学才有资格要求时代认可和尊敬;正因为有益,文学才能面对那些已经创造了伟大作品的先辈而毫无愧色。写作有益的文学,就是要求一个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放弃与之相抵触的一切其他要求,为这一壮丽的事业献身。这个简单的要求可能显得朴素和陈旧,不如别的文学观念时髦和前卫,可就是这个再朴素不过的简单要求,决定着好文学和坏文学的最后分野,足以帮助写作人在历史的广漠时空上为自己的文学找到清晰的坐标,确保他们在眺望传统的时候不被文坛瞬息万变的纷纭万象所遮蔽。
正因为要创造有益的文学,所以在生活中劳动着、爱着、恨着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理应得到文学应有的重视。在托翁看来,那些对维持生活的劳动一无所知的统治者和有钱人所体验的感情比劳动人民所固有的感情要少得多,贫乏得多,下贱得多。他说:“一个劳动者的生活包含着接连不断的各式各样的劳作以及与它有关的海上和地下的危险,有辛劳的跋涉,有跟老板、头头和伙计的交往以及跟别的信仰、别的民族的人的交往,有跟自然的斗争和跟野兽的搏斗,有他的家畜要饲养,有他在森林、草原、花园、菜园里的辛劳的活儿,有跟他妻儿的相伴不仅把他们当成亲人,而且当成工作中的同伴、助手和接班人,有他对一切经济问题所抱的态度,他不把它们当成高谈阔论的对象,而把它们当成跟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生死相关的问题,有他怡然自得与助人为乐的骄傲,有他休息时的娱乐。所有这一切都渗透着对这些现象所抱的宗教态度,像这样的生活在我们这些没有这多种趣味和缺乏宗教理解的人看来是很单调的,它和我们的生活(不是劳动和创造的生活,而是享用和毁坏别人为我们造成的事物的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享受,微不足道的挂虑比较起来似乎是单调乏味的。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所体验的感情是很重要、很多样的,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的一切感情几乎可以归结为三种低贱的并不复杂的感情:骄傲、色情和厌倦。”
正因为要写作有益的文学,托尔斯泰对艺术在他那个时代的蜕变深恶痛绝,忧心忡忡。在一封信中,刚刚写出了《战争与和平》的青年托尔斯泰表达了他的困惑:“艺术,变得越来越特殊,满足越来越小的圈子里的人的需要,变得越来越自私,达到了发疯的地步,因为疯狂不过是达到最后阶段的自私。艺术达到自私的极点便是发疯。”在《什么是艺术?》一文里又说:“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个荡妇。……真正的艺术品只偶尔在艺术家的心灵中产生,那是从他所经历过的生活中得来的果实,正像母亲的怀胎一样。然而伪造的艺术可以由师傅和艺徒们不断地制造出来,只要有消费者。真正的艺术不需要梳妆打扮,正如一个被丈夫痛爱的妻子那样。伪造的艺术好比一个娼妓,她必须经常浓妆艳抹。真正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那想表达日积月累的感情的内心要求,正像对母亲来说,怀胎的原因是爱情一样,伪造的艺术产生的原因是利欲,正像卖淫一样。真正的艺术所引起的后果是把新的感情带进日常生活中来,正像妻子的爱情所引起的后果是把新的生命带入人世一样。伪造的艺术所引起的后果是使人堕落,使人对享乐贪得无厌,以及使人的精神力量衰竭。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应该知道这一切,为的是能把自己从这腐败和淫乱的艺术的污秽洪流中拯救出来。”
托尔斯泰说:“新东西在哪里呢?那应当推动社会、向社会指出它的缺陷、打开人们眼界去观察内心世界的新现象、指出人们道德完善的新道路的新东西在哪里呢?在他们那里这种新东西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当代作家全都写得引人入胜,并且大都有爱情纠葛、女人、各色猎艳奇遇,写得很露骨……这些作品哪里有什么思想?你读着读着,不禁会问:‘一个人干吗要写这些?干吗浪费时间埋头工作?’回答是现成的:或曰扬名,或曰得利。两者都是可怕的和肮脏的。”又说:“如果诗人们对你说,他们写东西是‘为艺术而艺术’,请你千万别相信他们。不对!他们或者为名为利,或者一门心思要别人谈论他们,为他们喝彩。我自己就写了许多东西,坦白对你说,因为我以前也造了孽,也一心要别人谈论我哩!”
托尔斯泰断言:“艺术作品中主要的东西是作者的灵魂……”
在世界文学史上,列夫·托尔斯泰属于那种罕见的巨匠式的人物。他和另一些在当世名声很大、在身后却湮没无闻的人不同,而是越看越高大,越看越令人喜爱和敬重。他之令人喜爱和敬重,不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有关文学的真理,更主要的是,他还是这些真理的忠诚实践者;他是一个言行合一的作家。他不是写作,而是将写作作为完善人生的手段。托尔斯泰永远不为卑鄙的欲望写作,仅仅为永恒的生命写作,写作只是他参与生活的手段。在漫长的生活道路上,他真诚地体验,细心地观察,孜孜以求地探讨着道德问题、农奴问题、爱情和家庭问题、善与恶的问题、罪与救赎的问题,并因为世界观的巨大矛盾而深深苦恼,在理解和考察本时代生活方面比同时代人走得更远。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探索从来都没有任何做秀的成分,而是坚定不移,一往无前,不依不饶。他不是那种写作与生活分离的作家,而是以一生实践着他所信奉的那些生活真理,而在文学上所取得的一系列划时代的伟大成就,使这里的论述更加令人信服,具有一种庄严感和不容辩驳的逻辑力量。
也许,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所面临的境况大体相似;也许,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是作为智慧劳动的严肃创造的文学,一种是没有任何理想和道德感支持的堕落的文学,而这后一种文学无一例外总是以时尚的面目出现,使那个时代真正的艺术家在进行艰苦的文学创造时,时常面对两种文学的尖锐对峙,并不时深感困惑,陷于孤独。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这些话,好像不是在谈论一百多年前的俄国文学,而是在谈论中国当下文学的现状。
———————————————————————————————————————
①本篇所引托尔斯泰语,均见《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漓江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