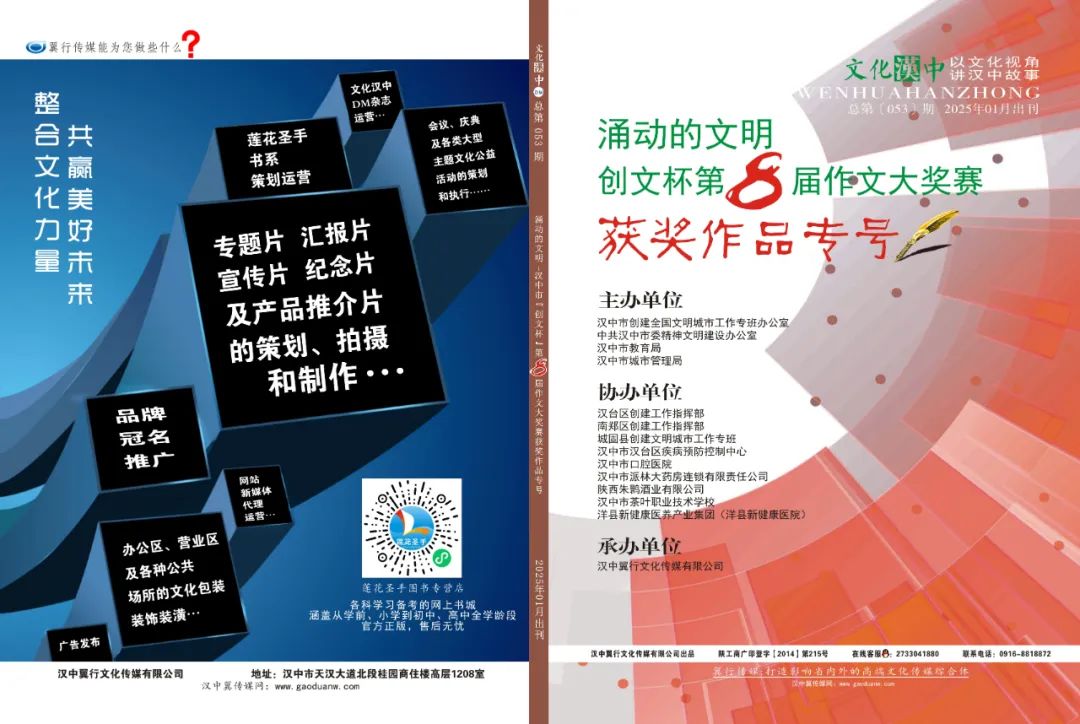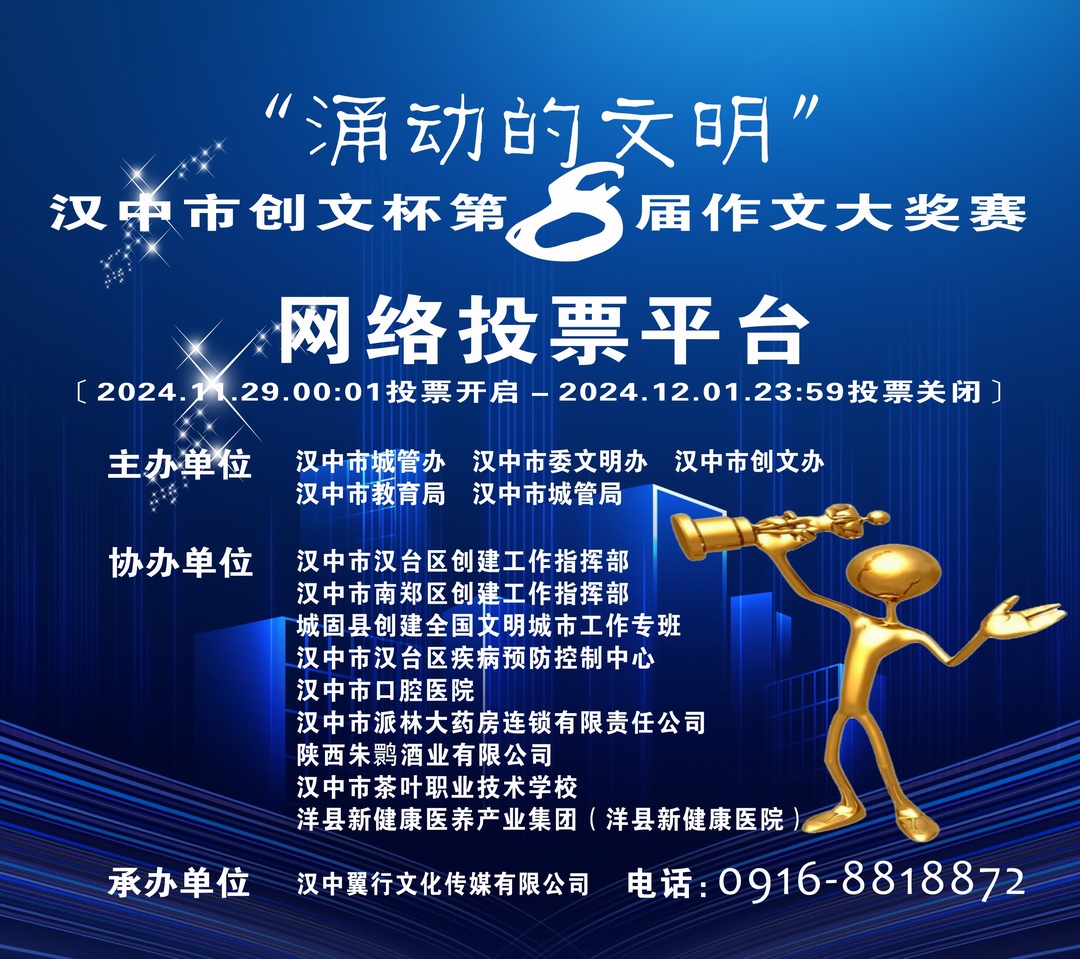神性写作为万物立言(第四章)
第四章 诗歌的乱世,神性写作可以大有所为
10、伪命题批判:神性不灭则文学不死
一位沉默已久的诗人忽然走了出来。他说:“文学死了。”并且煞有介事地列出了文学已死的十四种症状。一时网络哗然,从而引发了一场继恶搞赵丽华之后的网上大讨论。其实,文学怎么会死呢?我们并没有接到文学已经死亡、必须为它送葬的讣告。文学是自在的,野生的,拒绝的,顽强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力量的证明。我不相信文学会死,就像不担心青山会死,苍天会死,大海会死,星星会死,上帝会死!当然也有人说,文学真的会死,以往在中国已经有过很多这样的先例。他们说,文革十年,中国文学全面绝收,还不是等于死了吗?他们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两个文学的高峰之间都曾有过长长的低谷,在那些隧道一样漫长的谷地里,文学完全没有希望,也没有亮光,没有一个伟大的姓名,相当贫瘠和荒凉。他们说得很对;这样的事情以前有过,以后仍将会有,但不能据此断言:文学已死。也许,跟风的文学、媚俗的文学、迎合时代低级趣味的兽性文学,可能红极一时,可是时尚一过,说死真的就死了,因为它的声望并不是来自文学,这样的文学不是文学,我把它归类为“无效写作”。文学它有时候看起来死了,可是很快它又活了过来,平地里创造一个新的高峰!文学永远充满了变数,充满了奇迹,永远不可预料,没有奇迹就不叫文学!文学的荒凉的年代,每时每刻,都回响着对于奇迹的吐血的呼唤!也许,我们可以据此得出结论:判断一种自以为是文学的文学是不是真文学,不看它的宣言,只要看看它会不会死就行了:如果过一段就死了,它就不是真文学,只是伪文学,因为只有那些横跨时代和历史的文学,才配称为真文学,反之则绝对不是。我理解,这个诗人所说的“死了”的文学,很可能是背离了文学本质的伪文学!神性写作并不认为文学真的会死。神性写作的信心,来自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我认为,文学可能会在一个时代歉收,甚至全面绝收,却绝对不会死掉!它在一个时代歉收甚至绝收,也不是因为文学已死,而是那个时代的作家缺少才华,或者误入歧途、浪掷才华,或者虽有才华,却背叛了文学,失去了对神性进行指认的能力!文学并不神秘,但却根基深厚,担心文学会死,纯属庸人自扰!
诗歌不会死亡,因为神性不会死亡。诗只不过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赋予世界的性质,神性不灭,则诗性不灭。我注意到,在使用文学这一概念的时候,人们通常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用来指称作为绝对真理的文学;一个被用来指称文学的文本,正是它们构成了文学的物理存在。在讨论文学是死了还是活着的时候,得先弄清楚:什么是文学?前者还是后者?你指的是哪一种文学?我们习惯于把那种凝结着文学元素的文本称作文学,却忘记了作为宇宙大块文章的本来的文学。因而,在感叹这个年代杰出的文学文本何以如此稀少的时候,匆匆忙忙跳出来断言文学死了。事实上想要消灭文学真是太难了,因为想要消灭神性真是太难了,比创造神性都难。如果有人执意要消灭神性,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一定会很快发现,神性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就像一个愚妄的人宣称要消灭大海的光芒。一块玻璃打碎了,可是只要有恒星的光源在,每一片仍将闪光;一块石头你把它研成粉末,撒在大地上,它每一粒仍然携带着石头的完整信息。你把整个世界消灭了,它却在一瞬间变为巨大的能量,意味着一个新宇宙的创生,因为能量与物质守恒。神性是世界的性质,要消灭神性,除非先消灭世界。创世难,毁灭世界很可能比创造世界还要更难。文学是原在的,美是原在的,诗是原在的。所谓文学,只是绝对真理在美学向度的呈现,它与主宰宇宙、充塞万有、永远鲜活、沛然乎遍布宇宙万物的绝对真理同体,来自同一个地方!文学就是文学,既不可能被创造,也不可能被罄尽,只能被发现和指认!文学独立于人,独立于时代。文学在人类产生,被人类感知,人类的生活作为存在的一部分,构成了我们所谓文学的核心部分,那是因为它与人类切切相关。但文学是自在的,并不以某一时代的存续为依据。文学大于人类,也大于时代,它以罕世大美穿越一切世代!文学既不被增加,也不被减少;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既不上升,也不沉沦;既不明亮,也不黯淡;既不点亮,也不熄灭;既不生成,亦无所谓死亡。它就是老子哲学里那个道,就是佛所代表的那一种充塞万有的伟大精神,儒家哲学里的那个仁,就像我们置身其中的茫茫宇宙!文学它一直就在那里,有一种安静的品质,任何时候都与人类同在!文学如果是水,我们就是里面的鱼,被水接纳和笼罩,水构成了我们的家园!文学的历史比能够想象的更早;以宇宙大爆炸为标志,文学与宇宙同时诞生,一次成型!文学要是死了,就是说世界死了;或者世界还没死,而能够感知文学的人类却终结了。文学是自在的,通常居高临下,每一代作家只能从自己的位置仰望它,接近它,试图对它作出令人信服的指认和挽留,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文学的首肯!文学自己存在,是文学家自己因为羡慕文学的荣耀而走近文学:诗人用诗歌文本指认,小说家用小说文本指认,艺术家通过艺术的语言指认!在这样做了以后,这些被称为文学家的人,通常会走到舞台比较靠前的位置自豪地宣布:他们是文学家,因为他们已经奉献了伟大的文学,并把这说成是他们刻意的“创造”!而文学默许了他们狂妄的说法,因为他们毕竟先于别人对文学作出了准确指认,虽然文学心里知道,它并不是产生于什么人的创造——但既然人们爱用“创造”这词,无妨允许。
所谓“影响的焦虑”⑧显然被刻意夸大了。在我们这里,没有了对前辈作家的敬畏,只剩下“影响的焦虑”之下的仇视,构成了一些诗人美学弑父的最初动因。这些人把与前代诗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对抗,由于自己存在,别人就不能存在;由于自己出场,别人就必须被逐出。诗人与诗人之间,当代诗人与前辈诗人之间,犹如敌对的军队,你死我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打倒成了使自己成立和得到推广的不二法门。也许外国的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却把它念歪了,他们在其中趁机塞进了大量私货。其实,我们不可能与前辈大师完全对立,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传统的主体。传统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包罗万象,泥沙俱下。有些传统,非常非常地坏,比如专制主义;有些传统非常非常地好,比如中国文化里那个道,在许多时候,它很可能就是绝对真理本身。笼统地反传统,只是青春期热病的症候:你反的是传统的哪一个部分?五四是彻底的反了,可是八十年后,我们看到传统又卷土重来。忽一日从南京跳出几个小丑,说中国文学已经“断裂”,当代和现代已经断裂,他们和另一些他们已经断裂,如果没有“断裂”,他们将制造“断裂”,结果不过是故作“断裂”状以耸人听闻,沽名钓誉。而其实,反传统的冲动也是传统,就来自传统的内部,是那个几千年来轮番上演的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的造反冲动。由于兽性写作的猖狂跳梁,当代诗歌里至今没有公认的权威人物。这使我想起东汉末年:汉失权柄,天下大乱,曹操出来了,袁绍袁术出来了,刘关张也出来了,诸葛亮也出来了,勇冠三军、但却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吕布也出来了,董卓也出来了,十常侍也出来了,他们都从自己的位置出手以期窥伺神器;孙策已经据有江东,而每一座山头上都飘扬着大王旗,到处都有人反上梁山。最没日月的手足无措,可是不甘寂寞,也拉几个人三五条枪,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这是一个权力的真空;大家一拥而上,把汉家的天下瓜分殆尽。诗歌也是这样,当文革十年过去,当我们恍然发现建国三十年没有诗歌的时候,大家如梦方醒,中国诗歌出现了艺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真空。这是一个诗歌的乱世,一个诗歌意义上的三国志和南北朝,可能要持续很长的一个时段。在一个诗歌的乱世,我们必须取得穿越的目光,它有助于我们打开创造封锁的结构。由于太过敬畏,以往每当面对创造的时候往往放弃了思考。其实创造是有层次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很多自称创造的诗歌要求进入文化,它们簇拥在时间的门前等待确认,最终只有那些确有创造的部分,才能通过时间的验证,跨入了文化的门槛。并不是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打开创造的硬壳,我们发现创造并不是一个平面,有贵贱等级之分,有质量高下之分,也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创造的复杂性恰与世界同构。创造是一个有硬壳包裹的核桃,里面有极好的东西,须得用锒头砸着享用。创造是一块石头,有的里面只是石头,有的里面包含着精美的玉和钻石,需要细心辨认和耐心雕琢。在所有的创造中,我只肯定那些有益于世道人心的部分,或者干脆不把有害的创造视为创造。在所有的创造中,神性写作只肯定那些积极的部分。神性写作决定把艺术的破坏性限制在零度以下。如果有人因此要把我称作一条出色的猎狗,我是承认的,我确实是一条出色的猎狗,已经锁定兽性写作,它们一刻也不能藏身。无论兽性写作披上了什么样的伪装,有了怎样的时髦变身,亦无论它们名气大小,甚至是不能动的权威,都不可能逃出我的法眼,我会一下子就把它们像拎小鸡一样拎了出来。感谢目前这一个诗歌的乱世,神性写作正可以有用武之地。感谢中国诗歌里一下子涌现出了那么多披着诗歌外衣的小丑级别的人物,我们陕西人把这样的反面教员称之为“霉脑壳”,这是一些兽性膨胀到极点之后难得的丑陋标本——从历史的角度说,从文学成长的过程说,在总趋向上,它们是时代的产物,很可能也是一次性的。随着人文意识的觉悟,人类自救意识的觉醒,继起的兽性写作坏小子们再也不可能有他们的兽性写作前辈那样的好运,在不知不觉之中,兽性写作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时代的风尚正在改变。后起的兽性写作小子们,我敢肯定,兽性写作的事业一定要葬送在你们的手上。随着神性写作走上中国文学的前台,你们的好日子也到了终点,一统天下的好梦,更不要再做。同时也要说到批评:中国诗歌的批评,对于兽性写作的畸形繁荣,你们是有罪的,因为你们与兽性写作眉来眼去、狼狈为奸。当他们披着诗歌和文学的外衣,当他们像黑暗中悄然发生的秘密运动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发威的时候,是你们急于从中找到最具革命性的微言大义,是你们用你们手中掌握的版面,为他们背书,与他们眉来眼去,相互利用,急急忙忙把他们写进了文学的历史,把他们说成不得了的人物。你们中了他们的奸计。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你们扮演了很坏很坏的妖精角色。到现在你们想要来洗刷你们身上的血迹,重提灵魂,这是徒劳的。你们断送了自己的批评前途,走在与神性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神性写作拒绝你们,既拒绝你们的身影,也拒绝你们的声音。神性写作宣布,你们的批评无效,你们的文学史无效。但神性写作只不过为中国新诗打开了新的可能,将写作从兽性写作的人质状态解放出来,并没有终结艺术的道路。事实上神性写作可以容纳无数杰出诗人及其理论家的天才创造,成长出属于自己的全国著名诗人理论家。我并不担心神性写作会没有更多的人追随;作为一种写作的真理,神性写作是客观的,我只不过赶在别人之先把它说出。
而我最感欣慰的是,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写作,都将向神性写作靠拢。即使没有第三极文学运动,即使我有一天宣布将第三极解散,未来仍将有人回到这样的写作。事实上,当代诗歌一直在为自己准备着新的可能,它以漫长的延迟和等待,为神性写作准备了最好的出场时段。通过神性写作,无愧于时代的庄严的文学正在产生——它属于时代,是时代文学堆积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11、有道德则有诗歌,没有道德则连稍好的诗歌赝品也不会有
诗是诗,道德是道德,严格说来,两者的确没有什么关系。道德以人为本位,基于人的价值判断产生,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道德之存在在于有用,没有道德人类社会就会乱套,到头来谁也别想好受。与道德相比,诗处在更高的层面,在另一个轨道运行。作为世界的性质,诗与世界同时创生。故而世界在,诗就在;世界的边界延伸到哪里,诗也就延伸到哪里。在很多时候,诗与世界其实是同一回事,不过是世界在美学向度的呈现。我们无意于在诗歌里建立宗教,如果要建立宗教,那么它一定是泛神教,因为神性没有一个坚硬的核心,而是弥散在天地万物之中,渗透在世界的每一个细胞,把这个世界充满。诗是客观的、自在的、恒定的。自创世至今,诗一直呆在那里,既不增加,也不减少;既不前进,也不后退;不为桀存,不为纣亡。是英雄还是小丑,是圣人还是恶棍,对人来说可能极其重要,对诗却没有任何意义,不影响诗的总量和体积。诗只是存在,没有用处,也没有目的。将道德加于诗,肯定是对诗的一种降低。即使有一天忽然道德全无,斯文扫地,全人类都变成了恶棍,诗一定还是诗,江河依然日夜流淌,阳光依然穿越宇宙,照耀万物!诗歌与道德无关吗?兽性写作者你们说得很对;不过这里另有说道,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在写作中表达兽性,通常是最省力的,因为它停留在本能的层面,只需对存在作肤浅的模写就可以了。读者只要到非洲的大沙漠,去听听野兽求偶的痛苦嚎叫就可以了,那样的叫声一定比下半身诗人的淫声浪语来得更加本真和精彩。但如果要表达世界的本质,不只是模仿这样的嚎叫,而且表达出它们所以是的原因和意义,就不能在写作中拒绝神性。神性之道即自然之道。老子没有把这个叫作神性,而是称作“道”,认为道在自然那里,认为人后天的努力,只能从道那里来,人后天按照道的原则所做的一切,被叫作“德”,故而“道德”在老子那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但是必须承认,上文所说的诗,与通常所说的诗歌作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上面所谈之诗,乃大诗,纯而又纯,与世界浑然同体,无始无终,无内无外,天然浑成,难分彼此;说它浓,它浓得化都化不开来,说它冲淡,却又冲淡得无声无嗅、无迹可寻。而体积又太过庞大,几与宇宙同构,不能直接进入文化消费。那种原汁原味的大诗,正因为上述原因,只有天上的大神才配享有。事实上,经由写作生产出来的诗歌作品,并不是原初意义的诗,只不过是诗的替代品,只是诗歌写作活动的某种后果,是诗人为顺利抵达大诗的辉煌彼岸而临时搭建的桥梁。诗人就为了这个工作而来;世世代代的诗人所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每一个诗人都从自己的位置向大诗眺望,完成它的一些细部,把这些细部做大、做好。从这个角度看,诗人都只是“大诗”的雇员,他们站立在自己的命运里,在那里生活和劳动,虔诚地等候“大诗”神灵附体,然后把“大诗”的密语记录下来。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真诗,只不过是诗的赝品。可你是人啊,你受到限制,能有大诗的赝品,难道不是很好?此外又能怎样,得不到诗的真品,你能拣一块石头去砸天吗?至此我们知道,在讨论诗与道德的时候,有必要先把概念搞清:你指的是哪一种诗;是那个高高在上、充塞万有、无所不在的大诗,还是那种有限的、具体的、由一个个活生生地存在于某个特定命运的诗人写作、不仅打上了时代印记、而且打上了写作者个人生活印记的被称为诗的特殊文本?如果是前者,肯定与道德无关;但如果是后者,则一定与道德直接相关。只要承认任何纯而又纯的大诗,都只能通过一个个在具体命运中存活的个人来实现,把它们变成一首一首的诗歌文本,则诗歌与道德的关系也就先定了。
结论清晰而简单:有道德则有诗歌,没有道德则断然不会有诗歌,连稍好的赝品也不会有!
道德是诗人进入诗歌的惟一途径,是诗人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万应法宝。先有神性修为的人,而后有神性之诗。神性写作认为,诗只是诗人向神性逼近的副产品,直奔诗歌反而没有诗歌。神性写作对于道德的强调是认真的,不是出于写作策略的某种权宜之计,而是写作的根本态度之争,本质之争。道德就这么重要吗?有人说了,好怕怕啊!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道德?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谁才是有道德的,而谁就没有?问得好,这些问题我也正在思考。我承认道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专家学者们为此撰写了无数专著,未来的学者还将写出更多。但我认为,要说简单也可以很简单。道德可以有不同的层面,道德的实践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但就其核心内容,却只在“利他”二字。谁能做到“利他”,谁就拥有道德,进而拥有诗歌;谁不能做到“利他”,谁就不可能拥有道德,也不可能拥有诗歌。无论是什么人,无论“利他”的道路多么艰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承认人不但可以利己,而且必须“利他”,你就已经踏上了道德的自我成就之路。“利他”是人格成就的起点,确保人把身体从与世界和他人为敌的位置移开,把人性中的兽性部分限制在安全的和能够被接受的范围以内。从这里向前,沿“利他”的方向一直走到底,那里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无我”。无我之境,即大诗之境——在那里,世间万物经由万千法门、历经千劫万劫、越过千山万水的重重阻隔而殊途同归,天下大诗与天下大德完全合一。世界的本质排斥“小我”,在美学向度它是诗,在道德层面它是善,在真理层面它是真。由此可见,道德并不妨碍诗,而是为我们打开了诗的大门。道德不但在实用的层面帮助人类有效地组织社会,而且帮助我们眺望诗、倾听诗、触摸诗、享用诗,将通常总是匍伏在地面的人类生活,与高高在上的大诗接通,确保我们尽量原汁原味、不被损失地把大诗的元素转移到被称之为诗的特殊文本中来,此即所谓“命名”。所谓优秀诗人,本义不只是在于他会将文字分行,而在于由于有道德的支持,他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童心,随时听到大诗无所不在的低语,为它感动,并一再诉诸诗歌写作的特殊活动。但我并不轻易地和人谈论道德。道德要谈,只能跟有道德之人谈。道德是另一套话语系统、另一种更高层级的生活,只供高贵的人群享有。在伟大的人们那里,道德产生刻骨铭心的良性体验,他们视道德为幸福的惟一源泉,对道德的严格要求充满了感激和敬畏,而不是恐惧和仇恨。他们知道,人性有许多东西与道德冲突,必须加以克制,才能与道德的要求达成一致。人性如果是一块指望成钢的黑铁,只能由道德的炉火成就,这里需要的是舍身的勇气和烧炼的功夫。他们可以不成名,却决不允许自己成就恶名,哪怕是以一个恶棍的名义永载史册;可以不必有诗歌写作,却绝对不能容忍没有道德背景的写作,没有道德背景支持的写作,只能产生垃圾和精神毒药。他们相信如果单是诗歌作品,尚不足以构成诗人存在的充分理由,只有大写的诗人人格,才是诗人留给世界的惟一真诗,这样的真诗将最大限度地逼近大诗,与永恒的大诗存在同构。基于此,有些人写诗,他不是诗人;有些人不写诗,他是诗人。所谓“功夫在诗外”,即是指诗人为逼近大诗所做的必不可少的道德努力。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写作实践证明,道德不仅是伟大写作活动的背景,而且是伟大写作活动的动力源泉。一个禽兽一样的人,只知道鸡巴和纵欲,既不可能看到大诗,更不可能对大诗产生敬畏,他那个“我”是无限膨胀的,有限的心灵被欲望的永恒要求充满,不可能为大诗留下空间。说这样的人能够听到大诗的天籁的音响,哄鬼鬼都不信;说这样的人忽然写出了旷世的杰作,哄鬼鬼都不信。诗当然需要技术,但诗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艺。没有强大的道德背景支持,从政不能是好政治家,经商不能成为大商人,做诗不能成为大诗人,充其量只能成为码字的工匠——他们码出的文字,要么一盘散沙,没有灵魂;要么也有灵魂,却只有恶灵,诗歌于是成为邪恶欲念的传声筒。既要从事诗歌写作的高难活计,又拒绝道德的加入,跟这样的人谈道德,无异对牛弹琴,是道德资源的浪费。有道德之人,你和他谈道德,他拿你当知音;无道德之人越是无德,对道德越是憎恨,因为道德无论以怎样的形态存在,总是最先伤害到他们。无道德的人你谈道德,他当你是跟他有仇,形同剜他祖坟。他们仇恨道德,有时并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怯懦——他们达不到道德所要求的高度。面对托尔斯泰、曹雪芹、莎仕比亚、鲁迅,这些人也感到庄严,可是他们倾向于仅仅用天才来加以解释,以为天才可以离开道德的母土独立生长,开花结果。在他们着力经营的地盘上,种满了这种被称为天才的小苗,既然道德是难啃的骨头,他们希望最好能够绕开。他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正是强大的道德背景使伟大文学庄严;更不可能真正理解写作——成圣的路有千百条,写作只是其中的一条,即通过写作回归大诗,与大诗的存在浑成一体。
道德永远需要,对诗人绝对需要。大诗可以凌架于道德之上,诗人的写作活动却绝不可以有片刻离开道德,相反只能在道德加入之后才变得庄严,也只有被置于宏大的道德背景之下才能生效。是不是强调道德一定会损害诗歌?由于道德的加入,诗歌是不是一定会变得不够纯粹?恰恰相反,大诗之境,即大德之境,是为天道。天道的统一性,有时真是令人惊讶不已:越是抵达至高的层面,诗歌和道德便越是高度重合,两者殊途同归。那些蘸着血液写作、为着人类伟大理想写作的人,总是最先得到上帝的召见,最多地听见大诗无所不在的低语。他们的幸运,即在于通过道德的修持,最大限度地接近了“无我之境”!将诗歌写作神秘化,无限地抬高,并不意味着距离诗歌更近。正如把语言无限抬高(“诗到语言为止”),把身体无限抬高(“诗到身体为止”),并不是真爱语言和身体——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怂恿下,语言一天比一天更加无法无天,直到有一天自己崩溃,成为一文不值的“口水”和“尿水”,在诗歌和文学里泛滥成灾;而无限抬高身体的结果是,为一些人钟爱不已、视为惟一快乐源泉、并作为新的美学原则被固定下来的“身体”,也没有因为被无限抬高而格外坚固耐用,反而成为欲望的符号,在过度的纵欲中过早地垮掉。把诗歌与道德隔绝开来,用诗人写作的有限的具体的诗歌文本偷换大诗概念,将只有俗人才能操作的诗歌写作活动无限抬高,与原初意义的大诗混同,这是一个阴谋。这和借口追求纯诗,把诗歌与人类的良知、伦理、以及公平和正义等核心价值隔绝开来、最终消灭诗歌同样道理。一些人试图通过这样的手段,把诗与道德割裂开来,将诗的生命掐死,使它失去批判的力度;通过抽空诗、无限抬高诗,来架空诗、将诗歌就地消灭。在做了这样的手脚之后,诗歌的清水就被他们搅浑了,即使为所欲为,也不再会有危险了。这些人有时也可能看到大诗在彼岸群峰之间闪光,但当有一天想到要实现一次泅渡的时候,发现面前的深渊实在太过险恶——放大的“自我”正如同垂死的红巨星,在将他们生命吞没的时候,也将他们的写作吞没。必得有圣化的人出现,方能有圣化的大诗出现。堕落是艺术家的一种姿态,却不能成为艺术的事业。神性写作要求诗人首先认识万物,走近万物,而不是远离它。要理解万物的大悲大苦和它的无限大美。在作对天地万物的享用的时候,时刻不忘我们只是听从了万物的派遣,万物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相反与我们血脉相连,不能站在敌对的一面来看待天地万物,只有丧尽天良、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责任能力的恶汉才那样做。他们把宝贵的生存,变成了一次永不厌足的索取过程。难道万物只是为我们提供一次挥霍的机会?难道我们要求一切,仅仅只是为了一次纵欲,然后去死?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世界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可能把世界据有。世界是铁打的营盘,而芸芸众生,都不过是流水的过客,不能把自己的看得过高。如果你是一位诗人,想都不要这样想。你必须是克制的,对天地万物保持着虔诚的心情,像朝圣一样走向万物,只有这样才能洞悉万物的奥秘,得到上帝的召见。也只有在天地万物那里,你的才华才能找到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天地万物既构成了艺术的素材,同时也为艺术提供源源不绝的原创活力。你不可能在远离万物的地方找到艺术的素材;再者你所谓的命名只能针对万物,与万物分离或与天地万物敌对的心灵,一定最先枯竭。当通过艺术的特殊宗教与天地万物合一,我们将走向强大。我不说神鬼;即使是被认为无灵智、无感觉的天地万物,也绝不会容许自己的生成物成为敌对的力量。它造就了诗人,还允许这些能写几行长短句并以为能事的人,成为与自己为敌的人们的帮凶。与诗人的成圣相比,渺小的成名是多么不值一提!虽然成名完全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些人投身诗歌和文学的直接原因。我说,可以完全不成名,让我们只与神性居住在一起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看成名:成名只是后天的附加,只是我们接近神性亦即绝对真理的副产品,最终我们说:谁脱离了欲望的人质状态,谁就距离成名近了一步。事实是越想成名,越不能成名。渺视神性,却又要通过写作的小道成名的人,把写作的目的设定为成名,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成名了,得到了成名所带来的很多好处,可是很快又被大众抛弃——因为他们不可能与神性实现有效的捆绑,他们的名是很不可靠的,最终穿不过时光的烽烟。人类的利益大于诗,绝对真理大于诗,更大于诗人名利的总和。人类不会允许某种写作活动背离诗,成为损害人类根本利益的力量。背离了人类根本利益,也就背离了存在的本质,背离了天道,逆人类精神运动的方向而动。这样的诗歌活动,应当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加以制止;而对“我成名哪怕他洪水齐天”、为了渺小的成名不惜拉全人类下水的诗人,应当以反人类罪进行审判,判他们上飞机从五万米高空作自由落体。当然人各有志;如果有人执意要将与天地万物为敌作为写作的事业,则这样的写作是注定要破产的,今日不破产明日也要破产,明日不破产后日也会破产。推动世界更快地毁灭的诗歌,是绝不可以久存于世并发扬光大的。
今天的中国,道德正在受到广泛质疑,诗歌界更甚。这也许并不奇怪;几乎每到一个大变动的时期,道德的合法性总要被揪出来,作为问题重新讨论一番。每当这样的时候,那些执意要拉时代一起堕落并从中渔利的人,也总是要跳出来对道德大加挞伐,这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固定动作。他们有时大喊大叫道德有罪,因为道德的严要求,在历史上曾经被野心家所利用,成为野心家侵夺民权、推行暴政的有力武器;有时则将道德庸俗化,大谈道德多余,强调诗歌身份特殊,不把道德从诗歌中连根剜掉,则食不知味、寝不安枕。他们希望藉此在诗歌与道德之间阻起一道防火墙,将自己反道德的极其丑陋的写作活动置于这堵墙的保护之下。兽性写作也难,对此我表示同情。问题在于这样做不仅徒劳,反而暴露出一副与道德为敌、对道德又恨又怕的小人嘴脸。当然也不要指望审判——道德通常自己审判,而诗人及其写作,退不可退,首当其冲。
12、为万物立言,首先为天地立心
既然神性先于写作,那么在我们之先,一定有神性写作存在。但是在后现代条件下,在物质主义狂潮甚嚣尘上的时候,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旗帜高高举起,并且强调到这样的高度,是第三极文学运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贡献。但它受到抵制,抵制首先来自诗人自身。事实上,兽性写作势力在诗歌界一直非常强大,他们要人有人,要权有权,受到市场的奖励和庸众的追捧,得到一些所谓名诗人如于坚之流的无耻吹捧。在兽性写作龚断下的诗坛,只有神性写作是他们不能覆盖的最后边界。神性写作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分裂的显形。创造奇迹不能指望别人——奇迹只能出现一次;这就是当我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以来,内心始终有一种内在的激情强烈涌动的直接原因。
我认识到,在一个无法无天的诗歌乱世,神性写作大有可为。我愿意重申《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中的著名判断:当代中国只有两种文学的尖锐对立:即神性写作与兽性写作的对立⑨。
为万物立言,首先是因为我们人自己需要,天地万物并不希望这么做。大音稀声,大象无形,没有人立言,天地自有天风大河,自有春华秋实、四时运转。圣人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⑩天地是不需要立言的,是我们自己需要;而写作作为一种艺术的形式,恰好满足了神性呈现的全部要求。天地万物是自在的,但我们清楚地发现了一个秘密,即它有一种言说的倾向,它总是期待和鼓励我们,因为它渴望被言说,这里为神性写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神性写作的使命是:答应天地万物,以万物之子的本来面目出场,面向天地万物,为天地万物立言。立言的本质是感受到并且说出。语言是人类的创造,是我们连接天地万物的惟一桥梁,可是语言只有与神性接通之后才能通灵,才具有光辉。写作是有限的,是后天的事物。即是说,无论你写作不写作,神性都一直在那里,它自组织、自存在,不为桀存,不为纣亡,是我们自己要与神性靠拢,凑了上去,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存在——包括我们的写作就不具有价值。我们看到这个,靠上前去要求接纳和承认,为渺小的生存取得神性背书。很多人不需要神性的背书,仍然能够活得快乐,他们遵循实用和快乐的原则,只管此生,不问来世,可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作为神性写作最先觉悟的那一部分,如果没有神性的背书,我们将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生命之为生命,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虚无,与神性相背离的结果,是使我们永远陷落虚无的深渊——这是我们不能忍受的,除非我们把自己降低成动物——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杀人机器。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一直这么向下,从神那里要求快乐,一直退到后现代主义这里。神性的含量不断削减的结果,是其中只剩下欲望,转而把欲望当成神。而诗歌作为对世界进行精神享用的痕迹,需要把那些目击神性的宝贵时刻,通过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因为太多的同类渴望交流——在某些时候,我们把它称作经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通常相互冲突,有些经验往往使我们远离神性,但我们相信,只有那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神性和凝结着神性晶体的经验,才最具有价值——正是在这个时候,诗歌作为一种艺术走了出来。诗歌走了出来,我们看到,它是最适于盛载神性的容器。在诗歌这里,神性与艺术合一,很多时候,诗歌的光芒就是神性的光芒,此外什么也不是。神性写作作为人逼近神性的自觉行动,主要的不是向人们提供知识,而是提供拯救的范本和启示。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自救的动作,它不可能拯救世界,但一定能够(也绝对应当)有效地拯救自己,通过拯救自己进而为拯救世界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范例。如果我们视写作为其他,一定有违天地万物,使写作变得渺小和下贱,甚至使写作变成恶的凶器。悲惨世界——悲惨是世界的本质,神性也是;如果把神性完全剥离抽除,则世界就只剩下悲惨,真是太悲惨了。自从世界存在的第一天,就呈现出坚硬的结构。对于天地众生,世界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天国,而是一个严酷考验的生死场。众生都被投进了这个磨盘,它一刻也不停地耐心研磨,直到把众生都研磨成齑粉,灰飞烟灭。生与死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语言。我们一刻也不停地离开大自然,分立出来,又一刻也不停地回归大地,回归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我们不知道世界如此构造的本意,但我们相信,世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享乐为指归,如果一定要这样理解,肯定是自做多情。我们不可能让造物主收回世界,对世界进行重新设定,目前的世界虽然缺点不少,可是它有法度、完整、丰富、广阔,并不缺少什么——以为万物皆备于我,想都不要这样想。你不这样想,就会发现世界的好,虽然你同时也发现了它的悲惨,悲惨得要命。但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机会,正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通过生育加入进来;我们加入进来,乃是为了认识神性、走向神性,最终与世界的神性合一。渺小的写作想要改变世界的结构是不可能的。连持续几个世纪的战争,千百万人参加的中国革命,以数千万人死亡为代价的世界大战,都不能改变,我不相信写作能够改变。写作只对你自己有意义。你必须通过自救然后救人,佛也是这样。佛如果不是首先实现了自渡,他如何渡人?你最好想象你只是为了自救才投身写作。你不是佛,但你是佛教里大乘教的信徒,你不相信大乘教,但可以是小乘教吧,最低限度你可以通过写作这种特殊的修为实现自救。写作为了自救而来;首先是为了自己,然后扩大开来,获得了普世的价值。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那些渴望自救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人们找到的某种具有参考价值的精神手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读者掏钱购买了你的诗歌。事实上,只要回过头来,你就会看到神性,那是一个散点透视的存在,就如同仰望星空,从每一个方向都有神性的闪光。神性有无数棱面、无数层次,包括最卑微的和最伟大的,最丑陋的和最令人心怡的,那是一个无穷繁复的立体,经得起从每一个方向的反复打量。你不要梦想着有一天与神性狭路相逢,但我保证在你朝向的每一个方向,都会有神性的闪光。万物乃是神性的符号。也许没有世界,只有神性,因为叔本华说,世界只是表相——叔本华是对的,虽然他极其错误地用意志取代了神性,对世界本质作出了完全不同于神性写作的悲观描述。
为万物立言,首先为天地立心。一旦诗人的心成为天地的心,艺术就在这个时候产生。有这样的一颗心,对诗人是很划算的。天地的心,是世界的唯一的心,也正是上帝的唯一的心,在世界严酷法则之外的那一颗柔软和温情之心,但这一颗心带上了每一生命个体生存经验的背景。但它作为天地的心是统一的,有着同样的结构——它统一于宇宙的神性。这是一颗发现的心,悲悯的心,大慈大悲的心,敏感的心,平静的湖面,随时为接受万物的疼痛而来,像高级的导体,将它们的每一点悸动都毫无损失地传导出来,确保它们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验的浆果,不时在人生的秋天跌落湖面,溅起层层涟漪,拓开全新的风景。它将是一颗包容之心,为天地万物同悲;一颗将个我的要求限制在合理范围并保持克制的心。一颗有这样的心灵的人,等于打开了幸福的可靠源泉,因为在茫茫众生之中,只有他最可能得到上帝的召见。它黑洞一样深邃,拥有搅动星系的力度,迫使所有的天体围绕自己转动。当拥有了一颗这样的心,我们将发现世界无往而不是诗,诗将世界充满,且不再是苍白的,而是有血有肉,具有大诗所能有的全部品质。这时候,诗人成为万物发声的器官(我们必须靠上去;就像是在追求一位梦中的情人。万物高高在上,而我们处在较低的位置,必须靠上去倾听它,然后说出;让我们的心成为万物的心,让我们肉体凡胎的身体,成为天地万物发声的器官)。神性写作主张,诗人的心必须成为天地的心,一经成为这样的一颗心就通灵了,就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的能力,我们的感觉就可以轻易抵达世界最远的远方。在此以前,我曾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到处走着看着,在书里去寻找什么写作方法,而没有想到我们本来都可以是大师的候补人选,因为神性写作的历史使命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它通向世界的大的学问,足以供这个时代一百个伟大的诗人成就。我也曾指望能有人代替我把这些全部说出,可是等了三十年,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真理说出。我终于明白——我等待的其实是我自己——我不过是那个最终说出了时代和诗歌深层需要的人。我是一个普通的诗人,可是我身负使命而来,已经与神性实现了捆绑;经由这一次捆绑,我成为诗歌里最幸运的人,这是一个老的第三代诗人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才华横溢的根本原因。为万物立言,这是我理想中的写作,也是我所理解的写作的本质——我的梦想是写作的普遍梦想。我们无意于为神写作;恰恰相反,我们写给人看,因为神是超验的,并不需要写作,也不需要诗歌,需要诗歌的是我们。但神性与人性相通,我们使用的可能全都是有限的材料,但却无不反映着世界的神性本质——因为神性,所以人性。我们写作,但在写作中我们看到了自己精神的投影。所有向神性逼近的努力都值得尊敬,所有向神性靠拢的人都是当代文学和诗歌最忠勇的勇士。当我们说出“第三极”这个词,通往神性的大门已经被我们打开,兽性写作的严密围墙已经被我们打开了很大的缺口。我们并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神性,而是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实践神性,实现神性在世界事务(包括诗歌写作)中的全面贯彻。人可能是低贱的,但通过神性写作,我们有效地提升了生存,靠近了大神的莲花的底座,而神最终将接受我们——包括写作。 2006年11月20日-30日初稿;2007年12月22日-28日修订,2008年5月6日定稿于汉中。随即首发网络,收入当年编印的《第三极》第2卷神性写作诗学理论专号,继又收入刘诚诗学论文集《绝对的力量——刘诚博客二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注 释:
① 刘诚:《诗是诗人面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就若干诗学问题答网友问》,见刘诚诗论集《先锋的幻想》,第402-43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
② 刘诚:《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见刘诚诗论集《先锋的幻想》,第27-92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
③ 刘诚:《刘诚访谈录:重返天堂之门——从神性写作到第三极文学运动》见《绝对的力量——刘诚博客二年》,第9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④ 刘诚:《地球:即兴的短章》,见《刘诚诗七首》,原载《延河》2006年7月号。
⑤ 《道藏》是汇集收藏所有道教经典及有关书籍的大型百科全书。据《百度百科》,道教初期除《道德经》、《太平经》之外,其他经典很少。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发展,各派道士撰写的经典日渐增多。《道藏》之名始见于唐初,已有近1300多年历史。今所见《道藏》,是由明朝第43代天师张宇初及其弟张宇清奉诏主持编修,刊成于明正统十年 (1445) 称为 《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神宗又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编成《 续道藏 》。 这部明代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装为512函,仍以《千字文》编号。明《道藏》的刻板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全部焚毁,印出的经书也只有北京白云观收藏的一部尚基本完整。20世纪20年代,上海涵芬楼印书馆曾借白云观所藏《正统道藏》影印,改为线装册页本。《正统道藏》内容庞杂,卷帙浩繁。其中有大批道教经典、论集、科戒、符图、法术、斋仪、赞颂、宫观山志、神仙谱录和道教人物传记等等,是研究道教教义及其历史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收入诸子百家著作,其中有些是道藏之外已经失传的古籍,可供研究古代学术思想者参考。道藏中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如有关医药养生之书,内外丹著作,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等,对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化学、天文学、气功、人体科学等都是重要的史料。1996年起,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主持编修《中华道藏》,以明代正、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了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对三洞四辅以外的经书,又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归类,共分七大部类,各部类所收经书,按道派源流和时代先后编排次序。历经数载,后于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
⑥ 刘诚:《命运·独对永恒》,见《刘诚作品(1980-2000)》之《诗歌卷·愤怒》,211-36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⑦ 见《圣经文选》,文庸编著,第6页,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
⑧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和最有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代表作还有《误读之图》、《西方正典》、《解构与批评》等。《影响的焦虑》出版于1973年,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诗人对诗人的影响。作者认为经典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本书问世后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文论界对其争论激烈,褒贬不一。
⑨ 刘诚:《第三极文学运动宣言》,见大型文学刊物《第三极》创刊号,第132页,第三极诗歌网、第三极作家群落联合编印,2007年5月出刊。
⑩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见《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