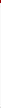资讯导航
资讯
头条
校园快讯
网站公告
专题
观察
视频
国际
汽车
楼盘
文化
财经
诗歌
小说
人物
网络
纪实
社会
旅游
娱乐
时尚
两性
美容
散文
“综合创建杯”第七届作文大奖赛(请按组别投稿)
灵异
科技
秘闻
杂谈
历史
读书
养生
探险
乡镇
趣闻
时装
观点
军事
爆笑
时政
猎奇
家庭
访谈
收藏
交友
揭秘
育儿
演讲
民俗
艺术
职场
讲座(作文方向)
优秀千字文
特约作文专栏
同题作文
莲花圣手:搞笑零分作文
优秀原创作文推荐专区
我的青春我的梦-校园演讲录
本月推荐:莲花圣手之星
原创作文自由投稿专区
讲座(口才方向)
情书自由投稿专区
汉中特产
随笔
教育
生活
体育
天汉女子诗社专栏
文库
广告客户链接页面
现代应用文自由投稿专区
莲花圣手周末作文训练营
陕西理工大学知行文学社原创作品专栏
莲花圣手作文大奖赛入围稿件(小学组)
莲花圣手作文大奖赛入围稿件(初中组)
莲花圣手作文大奖赛入围稿件(高中组)
镇巴中学特约作文专栏


|
王春贵
王春贵,号银屏山人,男,汉中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汉中市老年书画家协会会长。1946年12月26日生于安康石泉县城。1965年考入汉中大学(今陕西理工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定居汉中至今,2006年退休。擅长中国山水画、人物画及书法,兼好古字画鉴赏及收藏。1988年山水画作品四幅作为国家代表团礼品赠与巴塞罗那世界医学卫生代表大会。1999年山水画作品获国家文化部《世纪之光书画大展》金奖。2000年入编国家文化部《中华艺术人才大典》。2001年山水画长卷入选国家文化部与台湾文化基金会主办的《爱我中华》美术大展在北京美术馆展出。书法作品入选文化部人才中心与中国文联《迎奥运书画作品展》,先后在北京美术馆及莫斯科展出。2003年中国画山水长卷入展中国西部美术作品大展并入编该展作品集。2004年草书作品获陕西省文化厅群星展一等奖。多幅中国山水画作品被陕西省政府接待大厅、汉台区委会议室、勉县政府等重要公务场所及汉中各大宾馆在显要位置陈列。曾应省上特邀编著《汉中美术史》、《汉中书法史》。近年慢慢淡出展事,自称生活与心境可用“万籁无声月照窗”形容;声称书画自古文人事,准确点说是玩的事,不要说得太神乎,现在就是想把这事玩得更好一点。


坐看汉水云起时,漫卷诗书作丹青
王春贵:在书画艺术里修炼成精
撰稿/刘诚 美术作品/王春贵
知道先生大名很早,真正认识是在一次汉山游活动中——大家一起上山、一起下山,王先生一路点评社会人事妙语如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过数年,我的一篇诗学访谈引起先生兴趣,先生一时高兴,表示将有字见赠。书法家武妙华先生得知后于席间叮嘱:与其求字宁可求画,王先生的画更有价值。我呢见“有机可乘”,便顺水推舟,字也求画也求,“鱼和熊掌”一个都不少。因为是在席间,先生不便驳回,只好含含糊糊应承下来,于是开始了我与先生的一段深度交流。
一个周末,我敲开了临风尚居一栋住宅楼七楼的大门——王先生就住在这里。
先生径直将我领进了他的工作室——在这套住宅的第二层,西边靠墙一端,人字型的屋顶下有三只大吊灯,下面一张巨大的书案铺着毛毡,那便是先生平时写字作画的地方了。先生说,当时买这套房主要就是看中了这样一个结构,除了一个很大的书画工作室,还可以有一个很大的露天平台(屋顶),可供三五友人品茶纳凉坐地论道。平台周边养着一些盆花,据说出自女主人的手笔。纵目远眺,可以看到城东鳞次栉比的楼房,其间居然还有一大片烟树历历的田园风光——城市急剧膨胀的脚步,暂时还没有将它们完全吃掉。王先生对这套房很满意,虽然高一点,可是花一层的钱买来两层,足足280平方米,十分划算。而且结实——先生说,5.12大地震他就在里边,摇了一会儿,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先生说他现在退休了,生活很消闲,于名利无所求,只是游山玩水写字作画,生活和心境可用一句“万籁无声月照窗”的诗来形容。
在艺术之林里书画家最是自由散淡,在这里再次得到证明。不难想见,淡泊名利的王先生,如何在这座房子里漫卷诗书运笔如飞,化胸中丘壑为万卷山水。偌大的房子里,到处堆着一摞一摞的作品,一刀一刀的宣纸在靠墙一带堆得老高。高兴的时候,王先生拿出了他的宝贝,那是一些书画作品的图片,这些早年的作品有的是职业行为,比如大量电影海报,有的是多年的人物写生,有的只是为了记录当年的生活情境,每一张都负载着大量的记忆。近年先生已不再写生,所作多为山水长卷或厚厚的册页。谈到这里先生抱出厚厚一叠,都是新近创作的山水画长卷,动辄八尺整张、一丈二或一丈六整张。像这样的写意巨作,一般画家往往需要一周时间,先生只消三到四个小时即可一气呵成,且每一幅决不重复。我没有看到过先生作画,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朴素随和的画家,何以能够做到如此神速而又不损害艺术的质量。更奇的是,这些画都可以裁成多幅小画,还无损于它们的相对独立和完整。先生也让我看过一些小品,那些斗方、四尺整张各有情趣,在先生看来却都只是创作时热身的前戏,顶多不过属于积累素材、研习技艺的过程。先生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告诉我,若干年来每当有买家登门求画,他都这样一一摆开任由买家挑选,挑上哪幅是哪幅,就像一位摊贩将心爱的商品摆满地摊,任由顾客评头品足。但因为这些画有大体相当的品质,买家往往弄花了眼睛,最后反而拿走了主人认为属于中品的某一张。这些作品除了卖再就是送朋友,几乎每月都要送出去十几幅——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为此感到心疼,先生反而劝告女儿,不要把作品看太高,艺术需要流通,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自我封闭等于自杀。
先生于山水画师法现代大家黄秋园。黄秋园生于江西南昌一官宦世家,自幼酷爱绘画,少年家贫,进裱画店学徒,得览古今名作,刻苦临写,尤喜王蒙、石溪、石涛诸家。生前困顿,孤介不媚时俗,远离名利,不求闻达,一直受到地方美术界排斥,逝世五年后他的作品公诸于世,震撼中国画坛。刘海粟评黄秋园,认为黄画体现了中国人永不枯竭的创造力,工笔崇唐,底功扎实,以元人松秀之笔,取宋人构图,又得明末清初诸家之长,是自学成才的代表,王先生深以为是。于是潜心研习,从黄秋原画中吸取营养,坦承多年来受益匪浅。我于绘画外行,以外行的眼光观先生之所作,但见笔墨错杂堆积,于粗放中见精细,于静逸中见张力,线条和色块皆带灵气,一石一叶都有自己的逻辑和来龙去脉,看似乱花迷眼,其实有着极清晰的层次。先生擅长以繁复到无以复加的笔触,指认那些被大自然宏大形体刻意隐匿的秘密。观先生之小品,一溪一石,一草一木,廖廖几笔,尽得情趣;稍加点染,境界全出。观先生之长卷,如坐观茫茫云水,时而如山石疏林,疏朗空阔,给人极大的空间感的满足;时而极密极密,密不透风,如同构筑了一座线的迷宫,经得起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打量。且笔法多变,时而用彩,时而焦墨,万千世界奔来笔底,有一种排山倒海、气吞万里的气势。这里当然也有技艺但却极少匠气——艺术家必不可少的匠气(长期的技术训练),完全被情绪的张力激活和推动,绘画由此进入了某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
一般人谈到作画,总要说“胸有成竹”,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先生形容自己是“胸无成竹”,因为他的画皆信笔所至,临时发挥,画成之前,连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的走向。面对一张纸,先生一般总要精心画出几块石头和若干棵树木,相当于建筑物有了柱子,基本的材料有了然后尽情涂抹,使它浑然融为一体,因为大自然是模糊的,浑茫的。这里先生特别强调想象在绘画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说想象是一座富集的宝藏,画家再勤奋,也不可能把那里的宝藏开采完。就说山水画吧;既为山水画当然离不开山和水;有山总有水,山与水通过绘画交谈,不离不弃,就像是一对知音,有时谈得浅,就是见面相互打一声招呼;有时谈得深入,甚至深不可测,竟至于抵达哲学与宗教,这样的交谈没完没了,山水画也便没完没了。在先生看来,想象中的山水远比现实中的山水更高,更美,更奇崛,人们看山水画,主要是欣赏想象。由此先生反对一味写生,断言写生只是早期的必修科目,过了这个阶段还去写生,永远出不了大画家,因为写生的严格写实的训练限制想象。正如习书到了一定时候必得离开楷体,临帖、楷书只是早期学步,用于掌握汉字的基本结构,到一定时候就得毅然抛开。这些惊人之论可不是空谈,而是先生多年经验的精髓,有先生的书画实践佐证。一次,先生随采风团到四川,看到四川的画家都在写生,在那里写生甚至成为画家的美德,被一些画家坚持一生。先生不以为然,只是在那里看,拒绝动笔。到了笔会的时候,艺术家纷纷上场献艺,他发现那里一些很大的画家,画出的都只是小品,还每一幅都要摆弄很长时间,先生不禁心中一笑,不声不响地走上前去,四十多分钟过去,一幅气势磅礴的八尺长卷喷薄而出,艺惊四座。这还没完,从四川传回的信息是:你们汉中那个王春贵,那可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同样情境也曾在陕西省政府接待大厅重现——那里正面墙壁上一幅丈二巨作即出自先生之手,这幅画当年以四小时当场完成,曾让在场一些要人和同行目瞪口呆。先生说,他的画价格完全可以直线攀升,只消满足一个小小的条件,这便是从此搬到京城居住。先生自嘲,三百年后他的画可能要值一些钱,只是他看不到,这是画家的一个悲剧。又说,他一生都在画汉水——别人拿汉水当范本,我把汉水当载体,当一条有意味的“水沟”来画,现在看来要画一辈子。
王先生是安康石泉县人,早年教过书下过乡,在勉县工作多年,后调入电影公司,又调入市群艺馆工作多年,最后从那里退休。先生对汉水一往情深,从先生大半生轨迹看,汉水是母亲,也是一生事业的舞台,同时也是一生绘画灵感和素材的来源。先生还是一位有成就的书画鉴赏和收藏家,起初玩青花,因为陕南没有官窑,自认玩不到顶级水平,改为收藏名家字画。为了收藏,他可以立马放下饭碗,奔向某一座陕南小镇,因为忽然听说那里有一件陈年古物要卖;同样为了收藏,可以将一座56平方米的房以三万元的价格出手,只为了能够立马购得三幅王世镗真迹,理由是房子以后还会有,伟大的艺术品一旦失之交臂就永远不会再有了。和先生交谈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你完全想象不到在他那单薄的身躯里,暗藏着多少惊人的想法和美好的句子。先生也会不时冒出几句古诗,有些是从现成的古诗中拈来,有些则是出于自撰。比如这幅题写西乡午子山门的对联:“登极光明敢向芸生说大道,得真解脱须从午子看白松”,对仗工整,含义深刻,恰当贴切,极得境界。又比如在一次宴席上先生即席吟出的这样几句:“名山大,名山远,名山之中有景观。问君何日来陕南,好景未必在名山。”聊聊几句,友情、抱负和胸襟都有了,在座京城友人皆为之叹服。而这首五十生日感怀——“世人皆有石头记,为寻石头三千里。雪芹求石写红楼,我求此石梦山溪”,廖廖四句,活画出一生精神求索的鲜明轨迹。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艺术界天地之广阔可以供无数大家安身立命,偏偏老有人问他汉中艺术界谁是第一?先生说正应了列宁名言:“一个傻瓜的问题可以难倒一百个聪明人。”但先生说,还是有高人回答了这样高难的问题——一次有人问 “汉中书画家谁是第一?”张敏之先生答:“除了我不行,其他都行。”先生说罢大笑。先生知人论世,快人快语,入木三分,诸如此类的言论甚多。其妻曾警告他休得随意论人,因为他句句带“毒”。只是言语最迷人之处,也就在这一个“毒”字——字字入骨,决不枝枝蔓蔓,顾左右而言他,“毒”其实就是识见,洞见,才华,没有才华,想毒也毒不起来。我忽然想到,先生身边如果有一个文笔好的学生常随左右,那或许将是汉中文艺界的一件幸事——那些不择地而出却又转瞬即逝的名言警句、思想火花都可以被记录下来,若干年之后可望有一本王春贵版的“论语”或《世说新语》问世。王先生说,一定要注意身边的伟人,千万不要因为傲慢而与这样的人擦户而过。又说定居汉中四十多年,有两句话最为他所重视:第一句叫“狗眼看人低”,第二句叫“人穷志短”,至于背后的故事,任你去想。
坐看汉水云起时,漫卷诗书作丹青。这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言论家,一位心境休闲、无比自由、而又极富人生经验的老者,一个地方历史与传统文化、渊博高深的收藏鉴宝经验、言论家的深刻、道德家的博大岸然、诗人的机智与才情、俗人的生活智慧完美统一起来的人,一个半透明的文化与艺术的混合体,他以全部的生存拥抱艺术,在中国书画艺术的茧衣里修炼成精。但先生同时又是一位敏于发现、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为了阻止人炸毁曹操手书“衮雪”的超级文物“玉盆”,先生据理力争,不惜打110报警;也曾到处撰文游说各方要人使城固县韩家祠堂得到保护——这座原本湮没无闻的私家祠堂,现在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得汉中市委书记胡悦题匾“陕南第一祠”。最近又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让先生辗转不安——在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中,先生注意到一篇地方作家的文章,这篇谈论元史的文章披露出一个惊人的线索: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其实是宋朝末代皇帝的直系后裔,一条奇怪的血缘线索,居然将互为死敌的两大王朝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先生意识到这是长篇小说的素材,他希望能有高人进行考证,把它变成小说,再拍成电视连续剧,其敏识与乐于担当令人肃然起敬。
先生同时也是一位值得深交的朋友,在文化圈有着良好的人缘和口碑——他无求于你,也决不会亏欠于你,除了给你启发、给你愉快,总是有意让你得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