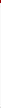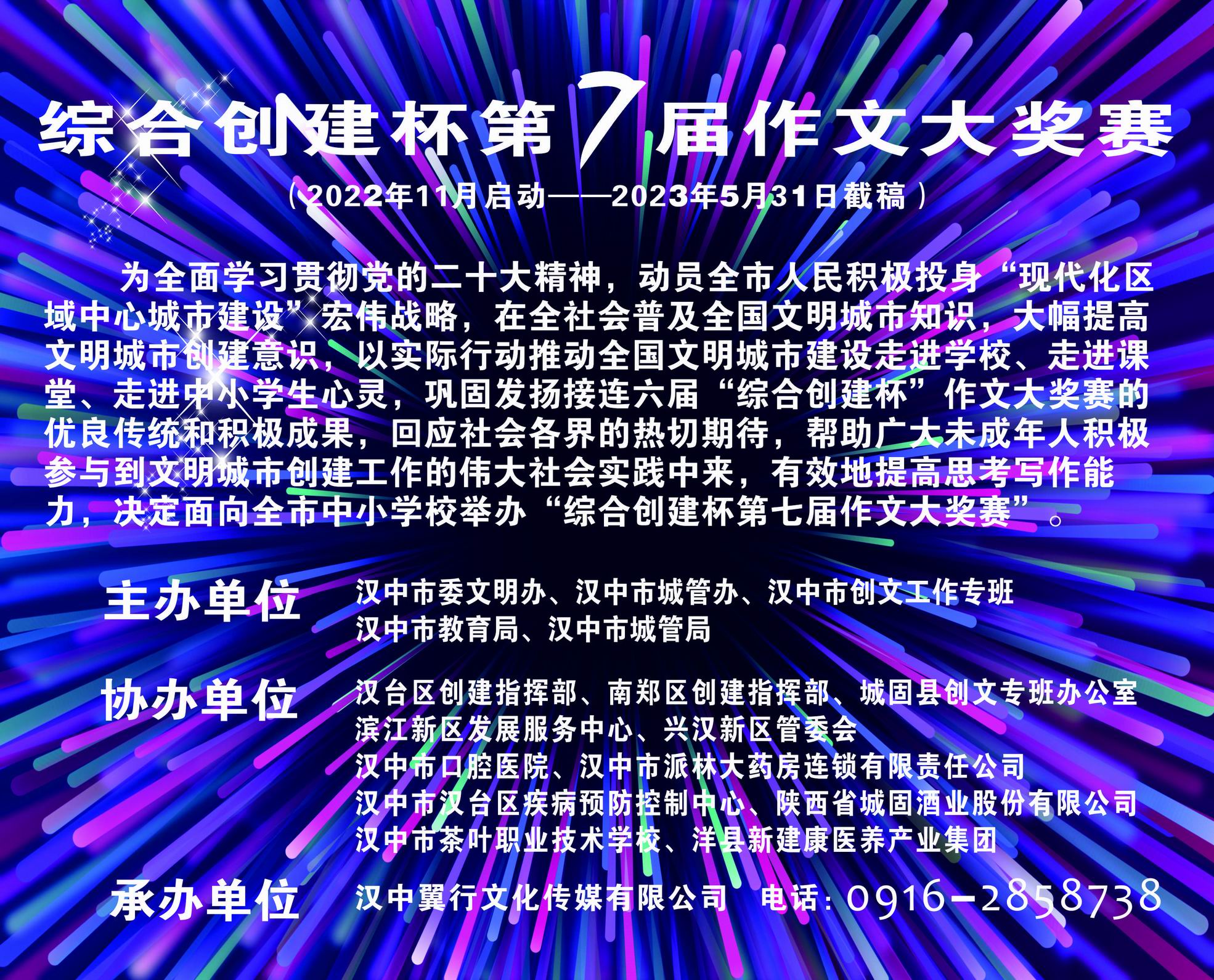王安忆发言
11月28日,2015年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上海爱马仕之家颁出。周小珊翻译的《6点27分的朗读者》获文学类最佳图书,许明龙翻译的《请中国作证》获得了社科类最佳图书,王名南所译的《当代艺术之争》则摘得新人奖最佳图书。
第二天,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邀请法国作家玛丽·尼米埃、菲利普·托赫冬和中国作家王安忆女士齐聚爱马仕之家,就“家庭、传承和灵感”为主题展开对谈,并由法国文学翻译家、本次翻译奖评委会主席蒲皓琳女士担当主持。对谈中,中法两地三位重量级作家从各自的家庭传承出发、结合不同的生活经历、灵感想象和具体作品,发表了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特见解和体悟。
以下为本次对谈实录
完全的虚构并不存在
蒲皓琳(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王安忆女士的,主要是关于她的小说《长恨歌》,我们知道《长恨歌》的标题取自于白居易的诗歌,王安忆女士童年的时候读到过这首诗,我第一个问题就想请问您是怎样在小说中进行传承的,譬如小说女主人公王琦瑶背后又藏着您个人怎样的经历。
王安忆:这个小说的名字叫《长恨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不仅是因为它是古人写的,还因为里面写了一个非常凄婉的爱情故事。用它来给我的小说做题目有一点反讽的意思,因为白居易写的故事是一个君王和他妃子的爱情故事,而我的小说里面写的是一个小市民的爱情故事。因为我是一个从事虚构(创作)的人,所以我写的小说和我的实际生活恐怕是距离比较远的。这个人物在我生活里面出现是(因为)一个传言,可是这个传言很奇怪,它会在我身边这些人身上变成真的一样。从听到传言到我坐下来写这本书已经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里面似乎这个传言变得越来越真切,越来越鲜活,越来越生动。写这本书距离现在已经有21年了,如果今天来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太残忍了,今天我写的话,可能我会仁慈一些。
我的意思是说人的经验其实不断地在修正你的生活,你的认识,会使一些很尖锐的东西变得温和。
蒲皓琳:我对于人物塑造的过程非常感兴趣,您刚才讲王琦瑶这位主人公很多是从传说,或者是故事中的元素(获得素材)。您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阅历的丰富,您在其他新的小说当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是怎样的过程?可惜后面有一些作品没有译成法文,所以我很想了解这个过程。
王安忆:我还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完全的根据我就很难无中生有,这个是我比较笨拙的情况。但是我又是一个虚构者,我又不太会把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写在我的小说里,不太允许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所以最合适做我小说人物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绯闻、八卦(中的)。我们这个城市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八卦,八卦特别的多。所以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讲,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八卦很有趣,正好处在真和假之间,所以你既可以顺着它的逻辑去想象,又可以给它添加一些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模糊的边缘,这个模糊的边缘可以不断地扩张。这种写作也有些危险的,因为有时候也会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说“你写的是我,可是你写得不太好,我很不高兴”。碰到这种时候(我)也觉得很难为情,觉得很对不住他。你知道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夹缝当中,我又要写得像真的一样,但是事实上我又不想伤害他。
蒲皓琳:玛丽,我看到您刚才一直在记笔记,我想您或许也是从王安忆女士的讲座当中得到了一些灵感,或许会成为您下一部小说的素材。您的创作正好相反,您是从一个非常真实,或者直接的经历来开始创作。譬如您的《沉默女王》,您的小说都是从真实出发。您的父亲过早地离世,您没有在童年的时候和他有很多共处,但是您通过写作来与父亲相遇,您可以(就这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玛丽·尼米埃(法国作家,作品《沉默女王》获得2004法国梅第奇文学大奖):我刚才确实是在记笔记,虽然我的作品是从真实出发,但是我觉得和王安忆女士非常的接近,因为(作品)也有八卦的成分。因为我是从很多传闻、很多故事当中来重塑一个父亲的形象。我们的两部作品《长恨歌》和《沉默女王》,其实从题目上来看就有点相通、呼应的地方。我这部小说的题目是从我父亲曾经给我写的一张明信片上的一句话当中得来的。
我其实对父亲没有任何有意识的记忆,因为我在五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当然也许我在身体当中存储着一些记忆,但是我有时候似乎是很有意识地去关闭这一部分。但是我是希望通过写作可以找回这个记忆,这就和王安忆女士提到的素材是来自于传闻和八卦(的情况)相去不远。我父亲的形象也是在这些传闻和八卦中得到重塑的。譬如我母亲给我塑造的父亲形象,那是一个非常光辉的父亲形象,她经常和我的兄弟说“我的父亲是多么深地爱着我们”,另外有一个公共的我父亲的形象,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所以在外界有一个非常伟大光辉的形象。另外也有一些来自比较远的传闻,这其中可能有一些比较残酷,比较暴力的部分。
对我来说我的写作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再认知的过程,这是一个反向的过程。一般来说都是父母生完孩子之后就到市政府去注册,或者是给孩子洗礼等等,以承认这个孩子的诞生。但对于我来说是反过来再去追认我的父亲。
蒲皓琳:您父亲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家,父亲的知名度可能对您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当时您第一部小说出版的时候也引起了媒体非常大的好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因为父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大家对你的期待值也会非常高。您的第一部小说当中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新的文学写作手法,您可以谈一下第一人称的写作吗?
玛丽·尼米埃:我们经常会像抽屉一样给作品去分类,我这个作品在法国被称为自传虚构小说,其实我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虚构的作品,但是能够放入自传虚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不可分割》,另外一部是《沉默女王》,但我自己更想将它们称为自传传奇小说。
有一个记者曾经这样评论我,他非常的犀利,甚至有一点恶意,他说“玛丽·尼米埃是(这样)一个小说家,她不看自己的肚脐眼,她只看自己的笔尖”,当然我也非常接受这个说法,也把我的作品,我的写作推向更远的地方,想从读者角度来重塑我写作的过程。
蒲皓琳:刚才玛丽·尼米埃女士讲到了虚构自传体,菲利普您也写了一部小说叫《外婆,外婆》,您是进入了外婆的世界。可以谈一下为什么您选择这个人物,一个和自己这么贴近的人物,而且把整本的作品都献给她吗?
菲利普·托赫冬(法国作家、戏剧家):我写这个小说的想法来自于我外婆入葬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经常睡在我外婆身边,我外婆经常打呼噜,有的时候声音很响。在她呼噜声间比较静寂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害怕外婆会死,想外婆会不会离开我。我15岁就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外婆就一直都活着。当我40岁的时候外婆去世,这个时候我很悲伤,尤其葬礼的那一天我感到非常难过。这个葬礼在诺曼底一个小村庄的教堂里举行,这个教堂很小,就装不下所有为外婆送行的人。我的外婆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并不是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的人,但是从葬礼当中我们看到她和世界的联系,以及她周围所有的人对她的爱,就这个时候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
蒲皓琳:在读《外婆,外婆》这本小说的时候,我看到您花了整整30页的篇幅,就像梳理了一张清单一样来描写外婆的厨房,阅读起来有一点身临其境的感觉,随着您的描写我们看到外婆的世界慢慢清晰起来,您自己也慢慢清晰起来,可以看到您自己的性情,您和政治间的关系、您和宗教间的关系、您对家庭关系的理解等等,外婆似乎就成为了你自我建构的中心,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些其他人对您也有这样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小说或者是戏剧的创作当中,也会以这些人物来作为中心。
菲利普·托赫冬:确实我在我的作品当中有很多关于物品的描写,我觉得我们在写一个人的家,这个家其实就是这个人物的内心。我就通过这些物品的描写进入了外婆的内心。这些物品,譬如说冰箱中的食物,扔到垃圾桶的东西,我们吃饭的方式,这些都背叛着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本来想用传记的方法,就像茨威格那样的写法,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等等。但是后来发现茨威格写得太好了,可能没有办法和他一样好。后来又想是不是要加上一些朋友,或者是邻居对于外婆的回忆,他们跟我讲述的一些东西。就像其他嘉宾说的,我觉得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在一张白纸上面进行创作的,完全虚构是不是存在呢?或许并不存在。其实写作就一是种述说,通过这个物品我就可以进行述说,因为这些物品至少我是触摸过的,有些甚至是被我弄坏的。譬如我们家里有一个放糖的瓶子,上面有一个女王的肖像就被我打碎了。通过这个物品其实我不仅是述说他们,述说这个世界,而且也是自我述说。这本小说是塑造了外婆的肖像,其实也是我自己的肖像,或者是我家庭的肖像。所以有时候写家庭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有的时候似乎感到总是和家庭内部的一些东西非常的远,但是通过这个写作我感觉我似乎拿到了一张护照,拿到了一个签证,带着它,我就把外婆带到中国来了。我的外婆只去过两次巴黎,一次是见她的朋友,她的朋友原来是参加抵抗运动的;另外一次是到法兰西剧院来看他的外孙,也就是我,现在我把她带到中国来了。
小说的灵感源于生活
蒲皓琳:在您的作品中有一句话,我非常地喜欢,就是“诗歌或者是诗意就是充满气味的童年”,您可以来讲一下这句话吗?
菲利普·托赫冬:我们怎样进入文学?我们觉得可能去阅读莎士比亚,阅读兰波可以进入文学,但有的时候很多东西可以给我们打开一扇进入文学的门,譬如餐桌就是这样一扇神奇的门。譬如看到餐桌上的苹果酒的时候,闻到苹果酒醉人的气息,我似乎立刻就进入兰波最终的意境当中去了。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中一些平凡的场景,譬如我仰望天空看到海鸥从我头顶飞过的时候,就会想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些诗词,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很安心,因为我和文学间并没有距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说得太多了,譬如我觉得应该禁止大家再评论普鲁斯特,每一次这样的评论都让我觉得离他很远,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我想说让我们来读他,不要先来讲他。我后来就开始偷偷地读了普鲁斯特,就觉得和他非常贴近。
我的外婆她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而且她非常地坚持,她有她的世界,她好像不说什么,但是在这种寂静中有一种梦在产生,有一种忧郁在产生。在诺曼底的雨中经常会有一种忧郁的情绪,这个忧郁的情绪可能对世界不会产生什么益处,但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和我们一样,有着一样的情绪,我们会发现一样的东西。其实这种寂静是好的,可以帮你发展一种梦。但是我的母亲和外婆正好是反的,我的外婆是空的,我的母亲是太满了,她一直在说话,不给我留下空间。后来我做演员时就发现,其实在戏剧当中空间非常重要。
蒲皓琳:我们刚才讲到了忧郁、安静,那么您在安徽度过了很多的时间,也根据经历创作了一部小说叫《小城之恋》,创作当中忧郁和安静是否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安忆:其实《小城之恋》更多是来自于我在江苏北部的一段生活,那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我当时是在一个小的歌舞团体工作。我身边有很多男男女女,他们充满着活力、充满着荷尔蒙,尤其是舞蹈,它有身体的接触。所以我就觉得这对男孩女孩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我想这部小说对于我来讲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要写身体,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气味,这种非常感官性的东西对于小说来讲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是很间接的用语言来表达。开始的困难是我进入不了他们的欲望,等到我进去之后就出不来。怎么样使他们最终摆脱这个情欲,而获得解放。我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让女孩子怀孕生孩子,让她安静下来。
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一个小城,因为我觉得这座城市给人们的欲望一种约束感,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压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的欲望就显得更加的焦虑了。
蒲皓琳:您的小说当中很多谈到情欲的,这对8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还是属于比较禁忌的话题。刚才您在讲的时候现场有很多听众都笑了,可能很多年轻的听众对当时80年代的氛围不了解。所以您的创作通过文学其实也给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门。
王安忆:其实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个前辈作家,他跨出了更勇敢的一步,他叫张贤亮,他写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蒲皓琳:那么尼米埃女士,您其实也创作了另外一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和您非常亲近的朋友,您童年时的一个朋友。通过这个小说您写了你们之间的友谊。但是你们的友谊是在大城市的背景当中发生的,穿越了不同时期的巴黎。您可以和我们谈一下这个双重写作吗?一方面写了友情,一种非常亲近、又奇怪丰富的情意,同时也描述了巴黎这座大城市。
玛丽·尼米埃:我这个小说叫《不可分割》,讲述的是我小时候的同班同学,这个女孩子我跟她非常要好,之后我们也经常用短信保持联系,直到现在都经常问“你好吗?”。但就是非常奇怪,我们俩后来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我成为了作家,但她却成了一名妓女,并且和一些吸毒、卖淫、经常入狱的人(混在一起),这些社会问题和她连在一起。
刚才这个人物的故事是前景故事,(小说)还有一个背景故事,就是巴黎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从上世纪65年到80年左右,巴黎的不同街区也变得非常不同,还有一些街区的解放,以及当时人们的模样等等。所以有两个故事。
刚才菲利普讲到(人)和物品间的关系,其实也可以延伸到和自然的关系,或者和城市的关系。因为在城市当中有建筑,也有不同的空间。我们人会与它发生关系。
文学的传承和父亲
观众:我有一个问题请问玛丽·尼米埃女士,当您写完这本《沉默女王》之后,会不会对自己这一代和父亲这一代人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譬如您如何评价出生于30年代的人,如何评价您这一代人?
玛丽·尼米埃:我可以很快很简单地讲一下我的个人视角。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国右派,所以坚持右派的价值,非常的男权。我就觉得我和这样一个政治立场是对立的,尽管我并不了解我父亲本人,但似乎我和他的政治立场是持相反态度的。所以我在想象中如果他在的话,在这一点上我肯定会跟他提出反对意见。(他们那代人)应该是战后的一代,非常的男权主义,非常享受快速的发展,大量地饮酒,发生很多车祸,是这样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是68年(左右出生),奋斗的一代,所以和上一代是不一样的。
观众:我的问题是关于传承的,我想了解代际之间的一种传承。今天我们讲了承诺和缺席,缺席在玛丽和菲利普的作品当中都出现了,而我对王安忆女士的作品不是那么的熟悉,对另外两位作家可能读的更多一些,所以就想请问一下关于传承方面的问题。
菲利普·托赫冬:也许我刚才也谈到了一些传承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个缺失。譬如说外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缺失的人物,我非常想念她。不管是近的还是远的,国家的还是家庭的,或者我们从职业或者从周围的朋友当中,其实我们都在寻找自我。作为一个演员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做自己”,譬如在演莎士比亚人物的时候你要尽量寻找到自己,其实我们在演戏的时候并不是凭白地创造一个新的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投射到其中,才能把这个角色演好。在文本当中其实也是通过文本来进行传递,来寻找自我。我想我的这个作品《外婆,外婆》,或者是《沉默女王》当中,其实都是有这样的缺失,这种想念,有这种传承的问题。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所有的文学,其实都是通过这种他者来进行传承,来寻找自我,都是同样的过程。
玛丽·尼米埃: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家庭、传承和灵感。对我来说我个人的情况可能是传承这一块比较的弱。因为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生存,通过灵感来生存,我主要的工作是通过语言和想象来进行创作,也可以说我是通过灵感来再创这种传承。我们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有一种传承,有一种记忆。当然可能这种记忆会有偏失,有错误。还有一种当传承比较弱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灵感来再现这种传承。这可能就是总结了我创作的过程。
蒲皓琳:在传承上面可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得到的一些东西,一些馈赠,另外一块是我们给予赠与的。作为作家可能是赠与读者和观众。从家庭来说,我能可能是赠与我们孩子的。您是怎样看这个传承?
菲利普·托赫冬:我只能讲讲我自己的情况。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和我的孩子保持足够的距离,有足够的耐心,不要去急于真的传承一些具体的东西给孩子。我的感觉如果是我们要追求去传承一样东西,实际上我们离传承的失败似乎已经不太远了。譬如我的外婆就从来不会去说她的价值观,譬如要有勇气,譬如过分赞美乡村——觉得这是一种真正生活的所在等等。她并不会去讲这些、传递一些说教式的话语。但她本身就是一种化身,传承的化身,是勇气的化身,也是一种稳定感的化身。对我来说可能有时候感觉有一些遗憾,因为她没有把这些东西告诉我,但是我通过我的小说创作来把它再现了。
王安忆: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最没有传承的人,可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城市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时候小时候看到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的照片,我感到很奇怪,觉得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竟然看不出一点关系。我的外婆在我母亲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外婆去世之后我的外公就跑掉了。到我父亲这边就轮到我父亲跑了,因为我父亲出生在新加坡,我爷爷奶奶都在新加坡,我的父亲似乎很不喜欢他们家,20多岁就回到中国大陆来了。但是我90年代的时候,第一次去新加坡,我的亲戚,就是我的婶婶,我的长辈们带我去扫墓,我就看到爷爷奶奶的墓碑上刻着我和姐姐的名字,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是有关系的。然后我就有一种兴趣去了解这四个陌生人。
玛丽·尼米埃:因为刚才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我有权开始提问了。我想问王安忆女士一个问题,刚才您讲了您自己的故事,但好像我在读您作品时没有看到您讲述这一段人生的经历。譬如您的“陌生人的故事”等等,您刚才也讲了八卦和传闻,我也从一些八卦当中了解您。据说您似乎一开始是想做钢琴家,想走音乐的道路。后来是弃乐从文了,是不是真的?您是不是想把这些经历写到作品当中去?
王安忆:这些经历也是零零落落会在小说中有所表现,但其实我作为一个音乐家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因为我没有任何音乐的才华。但是我的父亲母亲是从小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医生,因为他们都是搞艺术的,他们觉得在中国那一段时候的社会政治是非常动荡的,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做一个理工科的,科学性的职业,千万不要再去搞艺术了。
和您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右派,但是中国的右派和法国的右派正好是反过来,法国的右派是保守的,而我们的右派是开放的,正好是激进的。所以我的父亲就是右派人,因此我的母亲和父亲特别不希望我们从事艺术。
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我父母的梦想给打碎了,因为我就是中断了教育,然后到农村,整个我们这代人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我为什么写作呢,第一是因为我喜欢写作,第二写作是没有成本的。没有受到教育也可以试一试的,成为一名作家。
蒲皓琳:菲利普,您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呢?是为了传承吗?因为其实您在成为作家之前已经是非常著名的演员了。
菲利普·托赫冬:我觉得我是想通过写作继续来表达一些东西。我觉得无论是文学还是剧作,都是希望能够抓住自己,抓住人性的。在全世界每天都上演那么多的戏剧,这些戏剧的汇总实际上就是人性的汇总,它是以一种最正直的,最人文的或者是最诗意的方式来展现所有人的人性。作为演员来说,我要通过演戏,其实也是在述说。那么作为作家,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写作来满足我想要去述说的欲望,因为作为一个演员,我觉得是处于几个元素的交界口,我要去和导演沟通,要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也在和作者进行沟通,想要知道这个剧作家想要表达什么。之后就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来寻找到我自己表达的路径。譬如我可以通过某一个舞台的背景来进行表达,或者是通过某一个服装的元素来进行表达。那么我在写作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就是和自己在一起,我拿着一个手机、拿着一个电脑,我就是整个世界,我就可以进行自己的创作。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的,那种放松的感觉。
蒲皓琳:您最近有一个戏剧计划,演一个角色,这个导演选定了您。本来其实这个角色是由一个黑人演员来参演的,而您要通过化装来演这个角色。想请问一下您是怎样进入这个项目的?
菲利普·托赫冬:对我来说,这样的计划并不是打破一个禁忌的问题,戏剧是一块自由的领地,需要一种好奇,希望能够走向他者的欲望。我虽然不了解,但是我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和黑人这个角色之间的距离,与我和亨利五世以及一个英国国王之间的距离其实是一样远的。也许您会问“您有什么权利去演一个英国国王”,其实就像我有一天会演一个中国的剧本一样,也许我们都是没有权利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表演来了解他,所以重要的是一个参与的路径,而不是一个结果。我觉得演戏就像孩子扮家家一样,孩子会互相指定一个角色,你扮什么我扮什么。其实和演戏很像,他们也没有一个权利说这个小孩就能演国王,但是如果他可以演好的话,就有一些东西会出来。譬如有一天我有一个中国的剧本,用法文的话我也愿意尝试,如果我能够把握文本意思的话,我也能传递出一些中国剧本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一种想要了解的好奇心、一种欲望,而且是对于人文精神的一种好奇,也就是对他人的好奇,他人在写什么,他人是怎么样的。
在写作上面,有一些作家我读了之后,感觉他很有才华,但是不会激起自己写作的欲望,但是有些作家会激起你写作的欲望,譬如莎士比亚,我读的时候就非常想自己也写。我有一种感觉他写了我想写的东西,他用了很多比喻,一些文字的游戏,有的时候是一种重复。我有时甚至在感叹他与我想做的一个计划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会有这样的作家让人产生写作的欲望。
蒲皓琳:感谢大家下午参与这一场对谈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想通过不同的作家有两个概念可以浮现出来,大家多少都谈到这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童年,这个童年实际上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第二个概念是写作,有可能是文学的写作,或者是戏剧的写作。但是这个写作就是一块自由的领地,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传递我们自己,以及自己所接受的东西。
对话人:
王安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玛丽·尼米埃,至今一共创作了十三部小说,2004年法国梅第奇文学大奖得主,获奖作品《沉默女王》中文版已出版。
菲利普·托赫冬,法国作家,戏剧家,2014年获得莫里哀戏剧奖,出版《仿佛是我》(2004)、《戏剧之爱词汇表》等小说作品,《外婆,外婆》中文版已出版。
来源:腾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