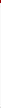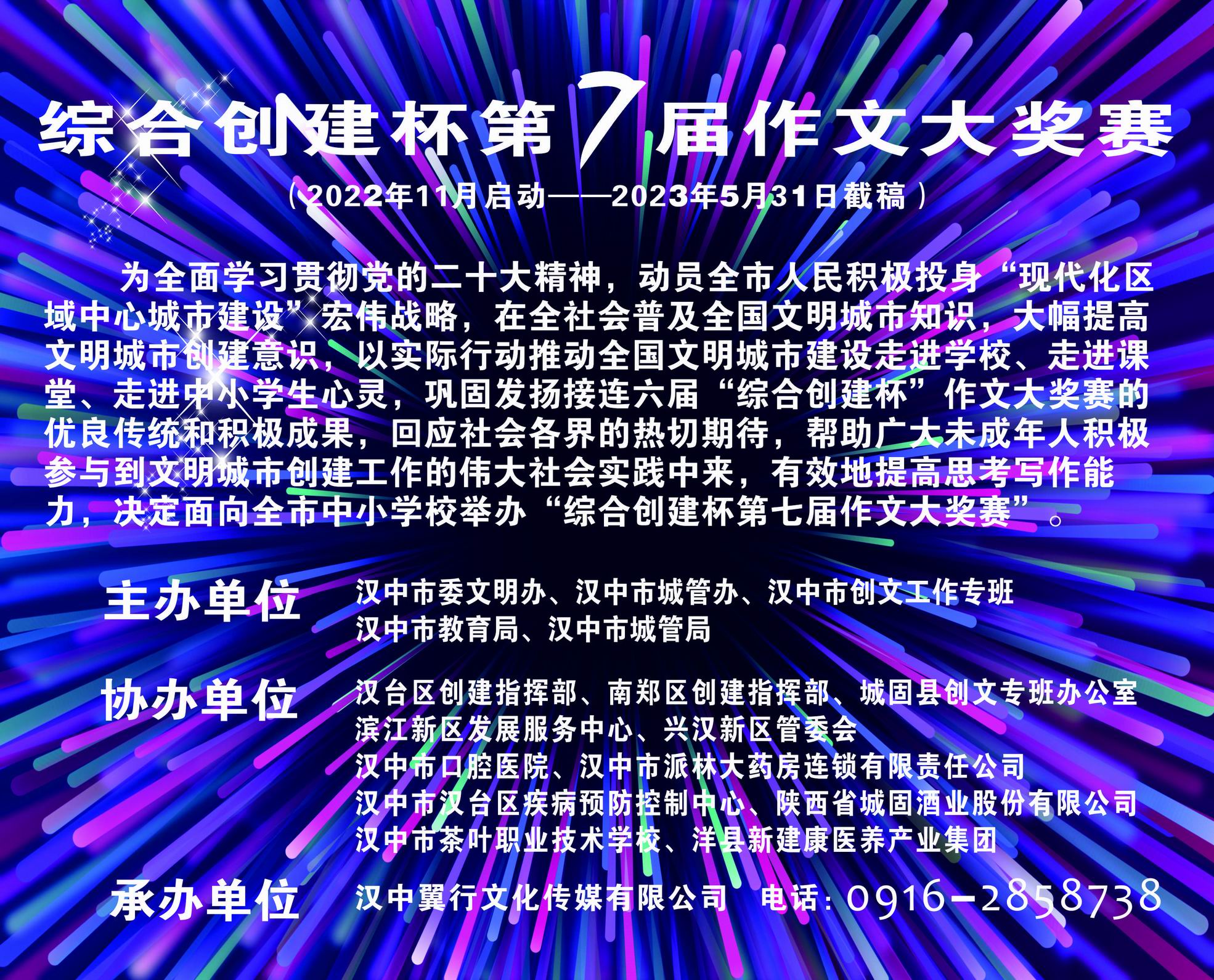活动速记稿
活动名称: 艺术家讲座:水调歌头 陈幼坚对话凌健
时间: 2011年1月16日 (周日) 14:00 –16:00
地点: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报告厅
(前面馆长讲话部分缺失)
翻译:这种融合正好和这次展览有共通之处,特别是我们昨天看过新的展览,装置的展览可能已经把艺术和设计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不用怕它们混淆。
翻译:再次请大家热情地欢迎凌健和陈幼坚两位先生。
翻译:既然一开始我们提问我就自己来提问一下,凌健和陈幼坚两位先生你们最开始是怎么认识的。
凌健: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坐在这里。我也非常高兴Alan,我的好朋友他在香港坐今天早上最早的一班飞机飞过来,跟大家见面,坐下来跟我谈我们的生活、艺术等事情吧。然后刚才我和Alan稍微见了下面,Alan问我要讲什么呀,我说真心话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先让Alan说,好吧,大家欢迎啊。
陈幼坚:大家好,我的中文不太标准,我尽量讲得慢一点。我今天生病所以我穿了很多衣服,因为前两天在香港感冒,突然之间又拉肚子,昨天晚上肩膀又不舒服。今天早晨一点钟我在打包的时候我跟老婆说如果我早上起来不舒服麻烦你打电话跟凌健说我过不来。(笑)最后今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觉得还可以就过来了。我觉得朋友就是这样子。我们英文说是unconditional,这是没想到的事情,绝非我来不了,如果还可以坐在这里跟他聊天为什么不过来,同样给我个机会跟那么多的年轻一辈的朋友聊天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我最近做了一个访问,那个记者一直追着我问,陈生你做得那么好,你的公司做得那么久,你是怎么按部就班来做这个事情的呢,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呢?这个月再过两个星期27号,我的birthday party在香港,我今年是61岁,真的人生没安排过,怎么出现这个状态我也不知道,就是随和吧。五年前,在北京碰到这个朋友,中间没有怎么招呼过,只是慢慢去看他的作品,心想去拥有,就聊天坐下来,就这样子过来的,真的没安排,对吧。所以你问为什么答应你过来,我觉得纯粹是一种感觉,我喜欢你,但我喜欢女人多一点,但这个男人我还是…。(笑)所以就这样子,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过来,觉得你的事情过来,真不好意思昨天开展没过来,真的昨天不舒服来不了。所以今天勉强身体状态(还好)过来,明天就走了。开心呢这样子最好,一个回忆。我很喜欢memory,很喜欢追求初恋first love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做项目就是这样子,每一个项目每一件事情我都追求这种初恋的状态。男跟女的关系是最好的。对吧?
凌健:对。Alan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我第一次见Alan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中国朋友特别少,因为我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嘛。所以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酒吧里边,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通过一个朋友之间我们坐下来随便聊天,我才知道他是Alan Chan。在这之前呢实际上我已经知道香港有个特别著名的设计师,因为我看过他logo的形象,特别特别传统,有特别有一种国际化的传统,所以在我脑子里面已经记得很深,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所以我们一见如故。我们非常高兴,喝酒,喝whisky我记得,抽雪茄,然后聊天,谈艺术,谈生活等等,好像他是一个好多年没见的朋友。我没有陈幼坚那么有名,所以他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搞什么艺术做什么,然后我也没带什么东西。我在我那个特别小的古老的手机里有一个特别小的照片给Alan看了下。Alan一看那个照片他突然就很激动,感觉很有意思,反正就一见如故了。他看了之后这张作品就记在他的脑子里了。事过一年之后,这张作品在New York的sotheby拍卖,这个作品就出来了。这个事情就慢慢继续下去了。过了一年我们又见面了,Alan特别高兴地说当时我看到这个画我真的不好意思说我真的想…
陈: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画?一方面是这个画有一个蛮特别的character,一个状态,我觉得艺术家会注意这是一个definition,这是你的作品,好像你给别人有一种状态,是别人可以拥有的,别人可以模仿的。他的画我不用介绍了,大家都知道是一种什么状态。很巧,你画的这个女生也是我认识的一个模特——春晓,所以我说这个女孩我不可以拥有,这个画我可以拥有吧。(笑)所以我想买,但是我很奇怪我永远没有勇气说要买你这个画,不光是你,这种事我从来没做过的,我没有这个勇气去说我要这个画,你卖给我好不好,我从来提不出来。所以我后来发现你去纽约拍卖以后就说唉呀应该跟你买应该可以便宜一点。(笑)所以后悔了,就这样子没办法了。
凌:我想你对女生也是这样,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表示你的感情。
陈:通常都是她们表示她爱我,我不会说出来。
凌:所以就是你不会说出来,就是人的性格决定人的一生嘛,基本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实际上,我还是喜欢谈Alan,虽然大家都知道Alan是谁,他的设计,他的才华,他在世界上的影响等等这些事实。今天我的水调歌头这个展览实际上在运筹上和Alan也有关系,当时Ada也在,我的画室里有一张画是特别亮的灰的调子,我们坐在画室,Alan看这个画,我也在看这个画,我们当时不约而同地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应该做一个镜面的作品。当时我说啊这个想法我已经想了很久,Alan也是这个想法很好,但是说完之后就过去了。我想说我们见面在一起总有好多话要说,我们之间有种默契,这种默契是一种生活和创作的状态。这个事情后来就这么过去了。
事过几个月我又碰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又跟Jérôme Sans有关系。当时我在准备水调歌头的主题,我一直在想怎么用什么办法将中国古典的诗歌充分表达出来,所以翻来覆去找了好多材料,改变了好多想法。最后有一次我要给Jérôme Sans报方案,我想我给他看水调歌头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讲嫦娥呢他是一个法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让我的助理在网上查一查有没有一个最好的英文翻译,然后找到了一个水调歌头的英文版,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汉语翻译大师吧。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方案给了我们的馆长,馆长看了这个东西呢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一个字他突然眼睛发光,他看到了moon in glass,然后在一瞬间我们就决定了ok这个展览名字就叫Moon in Glass。
所以刚才我就跟Alan说有好多事情都是不约而同的,好像在我们人和人之间有一种feeling,如果这种feeling是良好的话会引起很多创作的欲望或者感觉,或者把一个创作提高。在好多年以前,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好莱坞的朋友告诉我,你应该注意你周边的人,你应该知道你周边的人对你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我当时也特别年轻,二十来岁,也不明白是什么。谈到这个又谈到艺术创作的话题上来,从那个朋友告诉我之后,我个人还是真的非常注意我周边的人给我的良好的影响。所以这次请Alan过来也是想了半天,尤伦斯告诉我找一个人来跟你对话吧,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我也真的说不清是谁,后来想了又想我觉得我请的最佳的客人就是Alan,我今天也很高兴说了这几句。
陈:你太客气了。坦白讲这样子对谈我可能是第一次,以前一大堆人在互相聊很多次了,第一次跟单独的艺术家谈。他第一次问我的时候说要我过来做一个对谈我答应了,答应以后我后悔了,我后悔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曾经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话题啊,他说没有,就随便聊,我说随便聊怎么聊一个半小时,除非是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去吃饭可以聊。所以我一直在担心要说什么东西。但是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坐在这边很舒服。刚才他说好莱坞的朋友告诉他注意周边的人,我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但是我很挑剔的,我很清楚什么朋友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不会浪费时间在不应该面对的朋友身上。但是凌健聊的一点很有趣,他说会留意周边的人,他周边的人绝大部分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女孩子,这么多画为什么全是女孩子站在画上,为什么没有男人呢。(笑)想听你说一句,为什么全是女人,没有男人呢,男人还是和女人有关系的。
凌:没有没有,这个话题我们也谈过,实际上也有好多朋友其他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我记得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爱江山更爱美人”嘛,对吧,然后我们就说“爱江山更爱美人”,什么“英雄救美”,实际上那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爱情是真正能让一个人完全超脱他的本质的力量,上帝造成这样一种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延续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我感觉在爱情之上还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把“情”去掉,只有“爱”,可能这个爱实质上是一种信仰。谈这个东西好像有点儿夸张,好像有点儿像谈一个特别高的灵魂的东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关于谈到对于女性的爱,为什么艺术家那么需要这些女生,这个故事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从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到毕卡索到今天。我第一次去Alan的办公室也是让我特别惊讶,而且让我有点儿嫉妒,因为Alan的办公室所有的全是女生,非常漂亮的女生。我一进去我说哇Alan你太幸福了,我也希望是这样但是没办法,我想我作为男人和男人之间可以非常明白,说实在一点,爱不是一种性,爱是一种feeling,是一种内心的状态,所以作为艺术家,作为设计师,或者是作为音乐家,有时候他需要一种不平常的心态。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会分泌一些分泌物,这些分泌物是我们艺术家创作最根本的那一点,这个时候我们会突然感觉哇,你这个灵感是从哪出来的,实际上它是和周边的气氛有关,这种气氛会影响你每天创作的激情。
陈:当然我是百分之百认同我这个朋友说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创意人,不管是一个演员、歌手、平面设计师、做广告、写文案的、艺术家、雕塑家、油画家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我们是有理想的,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的话,我觉得你一定会整天不断挑战自己的能量,这才是最基本的艺术家应有的状态。如果你很快满足于目前的艺术表现状态的话,我觉得你很快会过去。刚刚说的那些他们喜欢挑战自己,喜欢美的东西。所有的创作是美的,这是我的看法。音乐是美的,建筑是美的,文学是美的,油画是美的,雕塑是美的,艺术家喜欢美的东西,这个状态一定有,没有这个DNA你怎么做艺术家。男人是一个猎人,是一个hunter,就是看女人啊,女生是美的。当然我不会不看男人,但是我同时在看女人比较多这是正常的。如果有一个你觉得是好的艺术家过来跟你说我对女人没兴趣,这个一定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有可能他在骗你,把自己关起来不给你看到。这是我的体会,也不是吹牛,我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艺术家不喜欢女人,为什么艺术家不喜欢漂亮的东西。那不简单了。女人喜欢帅哥也是正常的,哪些女孩子不喜欢好看的男孩,但是她对好看的男孩没信心,所以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找帅哥当老公,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觉得喜欢好看的东西喜欢女生喜欢艺术整天挑战自己是正常的一回事,只不过有些人不说出来,有些艺术家装模作样的,本身很高调的,装模作样很低调,这些人是我最看不起的。有没有说错?
凌:没有。
陈:我不是艺术家,我是做设计的。(笑)他们在笑是认同我说的话还是不认同啊。(笑)
凌:现在Alan开始激动了。我想是这样的,实际上说来说去艺术家是我们的职业,做了那么多年,做好这个职业真的需要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到底在哪里。
陈:我觉得艺术家不同的是挑战自己,有一个心态是不满足自己,昨天做的作品今天推翻了重来这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的心态,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做商业设计我经常告诉自己,每一个个案应该不要重复自己所做过的,但重复的因素是有,因为我们做商业设计有很多maketing,condition,调节和配料,不是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得有个权重要怎么推出产品、客户等等。但是我尽量在这个条井里面跳出来,想跳出这个框框,想做一些存在在这个方面的一种状态,我是讲整天去挑战自己。
凌:对。我现在也是感觉很长时间比如说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不出门,然后也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我有时候特别烦有人在我旁边。
陈:你很好啊,你还有调整可以停下来可以不看,我没有,我每天要上班,要面对没有品位的客户。
凌:实际上你这个工作,我个人认为非常苦。
陈:很苦啊,所以不多看美女怎么办,怎么生活。
凌:所以我知道你怎么去调节,我一看三十多个五十多个美女坐在那工作,我可以理解。
陈:还有一点我的办公室是很漂亮的。我的会议室是一个墙上面是密封的板,下面是透明玻璃的,所有的女生跑过去的时候我都看见她的腿在走动。我故意没去开会坐在这里,我坐在玻璃后面,顾客坐在这里他们整天看腿跑来跑去。所以她们都想办法穿的高跟鞋是最好看的最时髦的,她们觉得很骄傲很开心啊,她们开心,我们也开心,为什么不可以呢。
凌:对,所以你还是总是想到非常好的办法来…
陈:也没有故意,从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状态来做这个事情,我没有故意去做,我觉得第一我不想办公的开会的地方是密封的,我觉得不好,我不喜欢门的,我公司里面基本上是推拉门,没有关门的门,推拉门拉起来看不到门的,所以我希望我跟我的员工,我跟客户,客户跟我的员工有一个看通看透的状态,明白吗?
凌:嗯。
陈:你进来看清楚我是怎么回事,我也看清楚你是怎么回事,我很快认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开始工作,这是一种状态,一个brand,我们做品牌,brand经过这个包装告诉这个客户我是怎样一个人,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手段,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有手段呢,这个又不是害人,他看到美女很开心,比我还开心,他也不看我这个方案看外面的美女。
凌:(笑)所以天下的男人都一样,是这个意思么?
陈:天下所有人都是一样。
凌:所有人都是一样,这样的话又谈到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七情六欲了,这样吧,我非常理解你,我经常跟朋友说Alan看上去那么年轻,为什么那么年轻,我就想肯定是在香港偷吃什么良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俩有一张照片,我说哇Alan显得那么年轻,比我还年轻,我心里有点儿嫉妒,我就问Alan是不是吃了点良药什么的,他说没有,可能是这种对一个美的东西享受,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陈:绝对是的。你不开心还活着,不开心还有这份工作,你为什么不开心,但是我觉得不愉快的更要快快地做完,更快乐,捱在这里停在这里就更不愉快,快点将它做完就更开心。要正面地,面对着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人面对问题就不解决,待在这里停在这里不干不怎么做,我就会尽快干掉它,做完就过去了。我是这样的心态。人当然有不开心,有高有低嘛,低的时候就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要避开,这是我做人的一个态度。
凌: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陈:我觉得你要从一个很乐观的态度去想,有一天我一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今年我是61岁,有可能再过10年、15年、20年我不在了,我有这20年我要尽量去享受这20年的时光,我是这样想,但不代表我会去浪费这20年,随随便便就过完,因为我总有一天会不在了。我这样有可能会走得更快。我有这样的想法。
凌:我想就是说作为艺术家也是一样,你刚才谈的事情在我心里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中国了,离开中国的时候当时是80年代,很难离开中国,离开了以后到国外去也很辛苦。因为没有什么基础,没有朋友,没有钱,没有做准备,不像你们香港人还有一个好的环境,语言也不会,所以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了。当时我记得我父亲抗日战争时是新四军,我父亲一直非常严肃对待我,我走的那天晚上我父亲还有我妈妈坐下来,我父亲皱着大眉头说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走,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父亲说这个事情。
陈:当时他允许你走吗?如果他说你不要走你会走吗?他坚持说你不要走你会走吗?
凌:我还是要走。
陈:为什么那么坚持?
凌: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当时是80年代,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性去世界上看一下,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可能性,我们家也有我们家的故事嘛,我听我们家的人说当时抗战的时候,还有国民党共产党这些故事嘛,然后有些人跑到台湾去了怎么样,给家里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当时那个时代,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国家去别的地方好像是有一点犯罪的状态。
陈:当时你多大啊?
凌:二十三岁。
陈:大学毕业了。
凌:对。那时候我母亲问我你出去以后不能生存怎么办,你在家里我们还可以多帮助你,你想做艺术家嘛我们也没办法,实际上我父亲我想我做艺术家。
陈:你经济方面允许你这样离开吗?
凌:当时有一点小的朋友之间还有亲戚有一点帮助。实际上我父亲不喜欢我做艺术家,他的意思是可能是学医学等等这些事情可能比较好一点,我要走他也没办法。他说你出去没有人帮助你,你自己那么年轻,只是大学毕业而已什么都不会,那你出去怎么生活。当时我想我父亲说的也很对,实际上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我说无非只是在桥底下睡觉,我肯定饿不死,我父亲听了这句话非常难过,我第一次看见我父亲眼睛发红。
陈:当时那个年代如果你离开了国家允许你回来吗?80年代你走了,过了一年觉得受不了要回来可以吗?
凌:那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有问题,因为当时是上学嘛。然后我一走呢就是五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能有电话,但是很麻烦,没办法我只好每年过年前给家里寄一个小的磁带,因为电话很不方便,写信我这个人又特懒,感觉写信很别扭,觉得传递不了我自己的感情,我写东西感觉有点虚假,就不喜欢写信。我就录一个磁带,每年把那个磁带寄回来,一家人就在那听。这是过去的事情嘛,我说这个呢意思就是说实际上艺术家的创作和他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上次在今日美术馆里面有一个听众问我如果中国的市场不像现在或是去年那么好的话,你是不是还有信心和信仰来做艺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给我。然后我说肯定,无论这个世界变化什么样子我必须要做艺术,我不会做别的。
陈:你22岁的时候你不是艺术家,你是怎样的样子,头发还是这样长长的,有没有胖,穿得那么多颜色佩戴那么靓丽的那种,有没有你的老照片?
凌:(笑)没有老照片。那时候实际上很破。
陈: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吗?
凌:那个时候感觉已经是了。
陈: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给你多大的信心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
凌:我想可能是那个年代的问题吧,那个年代感觉肩负着一种重任,这种重任好像也是教育的问题。我记得我上大学之前清华北大它们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就是说去了清华去了北大好像就是说…
陈:跟别人不一样了啊。
凌:嗯,肩负着一个振兴祖国的使命。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特别的艺术家了,但是我现在想来那时也是很幼稚嘛。
陈:我觉得很正常,现在的年轻朋友一样嘛,当你毕业以后那一刻就觉得自己是艺术家了,但是艺术家层次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路途的前头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凌:对,我想可能一样。我在欧洲的时候,我经常在柏林大学有一点小事情,所以认识很多柏林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
陈:我相信很多朋友在这里包括我一样从来没有真的体会过,想听听你当初去德国的时候生活的状态,上学的状态怎么样,可以说一下吗?
凌:可以,但是这个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随便讲一个故事吧,上大学的时候不允许长发,不允许奇装异服。
陈:现在什么都做了。
凌:现在什么都做了。
陈:(笑)他是一个懒惰?的青年。
凌:当时长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陈:我在我21岁到26岁是长头发的。
凌:你也是长头发?
陈:嗯,在广州去打工的时候。回到你这边,跑过去的话呢,一开始是没有工作的。
凌:一开始是有一点点积攒的钱,学语言嘛,学德语啊什么的,反正这也坚持不了多久,然后就想办法要打工。但是打工呢,在80年代你们现在没法明白的确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要生存下去就要想办法去打工,语言也不好,那就去中国饭店,就做最低的工作,在中国饭店里面打扫卫生擦桌子洗盘子洗碗这些事情嘛。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老板是台湾的,刚开始我打扫卫生也无所谓,后来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说这个小伙子还挺努力,你可以去酒吧后面倒酒什么的,当时我长得还马马虎虎,也不是拿不出门去的那种人。当时他说如果你想在酒吧后面调酒或者稍微照顾一下的话,第一你要现在马上出去把你的头发剪短,然后我一听我心里就开始咚咚咚地想骂人,他妈的,我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院长让我理发我都没理,你这个做老板的洗盘子洗碗的还要我理发,绝对是没戏的,然后我说goodbye,bye-bye,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我就好几天没饭吃,但是我感觉还特爽,你说在北京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最高的学府,我们的院长让我剪头发我都没剪,你这个做饭店的告诉我这是开玩笑的,这种虽然是没钱或者是饿肚子,但是我感觉还是哇我还是特别相信我自己的。
陈:这是艺术家一种最基本的态度。
凌:这都是一些小故事,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一种信念,我想你肯定也有一种信念。在香港那么多人做设计,香港这样一个特别商业的社会,真的有才华的人也很多,然后这么多年,三十多年,是不是三十多年?
陈:四十年。
凌:四十年哦,sorry。四十年能做到这样一个水平,现在在大陆啊、香港啊,在日本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你也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可能会有一点儿相同。
陈:我从1970年中学毕业出来打工,去广东打工上班,到有自己的公司,大概三十多四十多个人左右吧。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司多大,有四十个五十个一百个从来没有,没有这个个计划要将公司做到最大怎么样,从来没想过,现在也不想。我很享受创意的过程,当然我现在很羡慕你们做艺术家喜欢画个画做个展览不行就不干了,多开心。哇,羡慕死我了。但是看这边的条件啦,但是广告公司给我一个训练是从一个概念出发,因为我们是卖概念的,是推广一件产品,推广一家公司,做形象的,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我是一个设计师,但是我有开始做一点点纯艺术的,但是我还是习惯,没有故意,每一个做创意的出发点都是从一个概念出发的,怎么去推一个概念出来,对方能明白,有共鸣,影响他,提升他,带他到另一个平台,这是我成天在想的一件事情。不管你看我的设计还是纯艺术类的都有这样一种概念在里面。最近这几年我来中国比较多了,一个星期来一次不同的地方,我第一次认识中国的艺术家是1991年,有一个做时装的女生,我跟她做品牌形象,她知道我很喜欢艺术就带我去圆明园画家村,当时有两百多个画家在里面,一个房间都很小,我看那些画,大头、牙齿我都不懂,以为是漫画,它当时是1000美金一张。
凌:1000美金一张?那个时候已经很贵了。
陈:我当时觉得贵。第一我不太认识纯艺术方面的,第二二百多个画家里面还1000美金一张太贵了,看了几个画家就没买下。但是跟几个艺术家约了一天凌晨12点钟去西单打保龄球,当时他们是很有型的,像流行乐队一样,穿皮裤,头发跟你一个样子也是长头发,皮衣,很有型的,我们去打保龄球。我觉得奇怪我回到这个村子里跟他们打交道吃饭什么的,也开始去收藏你们的作品了。我觉得我做人做事真的没有安排,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
凌:1979年来北京?
陈:不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86年。我第一个项目是给北京饭店贵宾楼所有的平面设计是我做的,它的logo还有印章餐牌是我做的。但我第一次来中国1979年当时没有深圳,坐火车去广州、苏州、杭州、桂林、上海,去了几个城市大概十天左右,每个城市去两天,拍了很多照片。
凌:你还有这些照片吗?
陈:还有这些照片,在我送给你的书里面还有照片在里面。
凌:那是你自己拍的吗?黑白照片。
陈:都是黑白照片,都是我拍的。我真的很奇怪,我走了一大圈,回来这里又跟艺术家走在一起,你问我有什么安排的时候,没有真的没有,这是随心慢慢走过来的,跟尤伦斯这边聊天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觉得我现在非常享受这种状态。人是不是应该没有目的呢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目标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梦想和目标中间不要故意去安排太多事情,勉强自己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是作为艺术家的话我是这样子,我觉得做人可以这样吧。
凌:对,我想好像有一点儿禅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在日本的茶道、禅宗这方面好像很有研究,是不是?
陈:我没有研究,比如说我在日本开茶馆是日本人投资在我身上不是我拿钱叫我做品牌形象推广,也没有故意去做很多事情,他们看到我,看到香港就过来找我。但在日本的工作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对事情的要求,坚持、保护,对文化的尊重,离我们很远,尤其是它对文化的这种状态是中国抓不住的。我去京都可以看到唐朝的状态,从很多方面,建筑、吃的、衣服、文化方面都有唐朝的状态在里面。我做很多项目都和中西文化有关系的,他看我的东西有一种wondering的感觉,他觉得也有日本的文化,当然日本的文化是源自中国的文化,他们对我的尊重,对我作品的尊重。就这样子,也是随心慢慢走出来的。那我在香港长大,在英国殖民地长大,应该是非常洋气的、洋化的、西方的,但是我是非常传统的,我对自己文化的根也是非常有兴趣的,享受的,有共鸣的,所以我非常奇怪的,我应该是非常洋气的,不光是在香港长大,在英国教育,在英国培训出来的。
凌:就是说如果是生活经历越多就越明白你刚才说的道理。生活经历多了艺术家或者是设计师等等他的创作实际上是给生活移植的,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比如说香港,香港也是有一个很小的故事,当时在70年代末,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的哥哥他偷渡香港,当时在大陆的宣传香港是一个天堂,他的哥哥偷渡六次还是几次全部没成功,最后一次好像成功了。他想了很多办法,自己做汽艇去偷渡香港。我说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说,当时在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都有一种感觉是香港是一个西方的社会,是一个灯红酒绿的社会,但是我一直没去香港,我从中国去了欧洲之后好多机会我都没去香港。
陈:没有这个欲望去吗?
凌:不是没有欲望去,我好像是要保留那种灯红酒绿、浪漫的我想象的香港的感觉,所以我就一直没去香港。很奇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欧洲我碰到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一看我就说你好像有一点特殊的东西,你这个脸相好像有什么什么痕迹,这个老太太好像是我们所谓的算命的,她不是用易经的算命办法,她是用星座。她说你有时间来我这儿我给你算一下,我说好啊,我也感兴趣。后来她就拿了我出生的年月日算出来说你一生做错了一件事情,你不应该在这里,你应该在香港或是好莱坞。她一说我感觉很纳闷,这个老太太有一种吉普赛人的感觉。我想可能有她的道理。然后在06年我才第一次去香港,一到香港我还真有种感觉,好像回到了我记忆中的感觉,到处很方便,吃得也特别舒服,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就突然又想起那个老太太给我说的事情。我也是讲一些故事说一些生活真的没办法去提前做一些计划。
陈:那从06年到现在你的创作里面有没有一点点受香港的影响和启发,比较微妙的一种感觉,有没有香港的女孩在在里面。
凌:没有没有,没有香港女孩。我现在还真的不明白香港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陈:我坐在你边上,我是100%的香港人,土生土长。那你觉得这种感觉在你人生的路途上有体会吗?你去过欧洲那么多地方比如说德国啊等等,你在回来中国做这一系列的人物的创作之前你不是做这一种状态的作品吧。为什么你回到中国会出现人物这个状态。
凌: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是一开始你提到的最美好的感觉还是初恋。
陈:美女还是中国最多。
凌:不是不是,不是中国的美女最多,是那种初恋的感觉。你提这个事情突然让我会想起这个事情来。离开了中国这么多年,离开中国时女性的形象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我能说这个因为当时你可能来一段时间就走了嘛,但是我的记忆非常深,好像是一个断片一样,突然这个片子断了然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片子又接上来了,这个时间的距离大概有二十年,中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04年05年那个时候又回到中国,我发现我周边的人完全离我走的那个时候有非常大的距离,他们有一种非常自信的态度,我特别欣赏年轻人的样子,无论男孩女孩他们有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我感觉就是因为80年代的慢慢长大,中国的经济发展了,各方面生活优越,家庭、教育等等,这种自信给我非常舒服的感觉。可能是和我有一种比较,我们60年代生的人,70年代长大,80年代离开,我们周边我生长的那个时间还是有很多杂七杂八没办法判断的内在的问题,社会给我们的内在的问题。
陈:所以我在看你的照片的时候从第一次在你手机上的作品到现在,我发现你的作品里这些女生的眼神好像都发出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代表你的内心世界和观众去沟通,每一个问号都代表一种生活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
凌:可能是一种一方面想享受今天的美,今天的状态,比我们的那个年代更强。
陈:但我觉得你的女生的美丽是危险的。
凌:危险?哪个方面危险?
陈:就是你想拥有她但是你觉得拥有她很危险。
凌:哇,怎么个危险法?
陈:我一直觉得第一她可能拿走你的钱,有可能拿走你的感情,也有可能破坏你的一切。只是这画给我的感觉是你很怕去拥有它,全都是美女,我觉得十个男生九个都喜欢看你的画,但是当我想拥有的时候有一种害怕的心态在里面,我觉得她会破坏我的家庭。
凌:(笑)
陈:我觉得她破坏我的一切。
凌:我现在明白了,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没那么成功去…
陈:我发现你在利用你的作品去发你的问号出来,因为你的作品在表现你的一种生活的状态,我的意思是你在创作一次画的时候,你利用这个美女去发出一个question,你的question是发自你内心的,你是怎么去选择每一个问号来表达你的状态的,你是去一个酒吧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个朋友,你怎么去找这个主题出来,你不只是画这个女人,美女美女,但是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我发现都有一个question。
凌:这个呢我觉得艺术家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有他疯狂的一面,没办法。我个人认为每一个艺术家都不一样的,他的外表,他的内心,他的语言,他的表现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有很疯狂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我有时候也有这种疯狂的一部分,就是我没有控制。
陈:我觉得是好事,不疯狂怎么做好艺术家。疯狂可以做艺术家,但是不疯狂怎么做好的艺术家呢。有时候我觉得疯狂是一种状态,是一种追求,一种寻找,一种心态上的表达,我是认同你这种说法的。
凌:有时候在欧洲我会突然疯狂,突然跟别人打架,这种事情会发生的。
陈:但你怎么控制在一个画里,创作是要一个很安定的很peaceful去控制这个感觉的眼神,比如说你画的这个眼神太厉害了,你不可多看她一眼,多看她一眼就感觉被她吸进去了,你疯狂的同时又要去安静,你怎么平衡这个状态呢。
凌:这个,这个我实际上也是情绪化的人。
陈:你做创作的时候喝酒或者抽烟吗?
凌:抽烟不喝酒。
陈:很安静的。
凌:基本上是这样的,我画画的时候抽烟也少,不画画的时候反而有点儿nervous,就是紧张。
陈:你可以很focus,紧贴在画板里一句话都不讲那种。
凌:对,我最享受的生活就是深夜,一个人在画室,听着我喜欢的音乐,画我的作品,然后我最享受的就是这个生活,我拿起我的画笔来有一种感觉,我心里突然开始平静。如果我不拿笔,我就啊。
陈:但同时间,你会记住一个现在你的疯狂,你会记住你要memory,你的这一个memory,当安静下来才会去经过你的画去表达。,是这样子吗?
凌:实际上我每一分钟,我想这个我们俩可能也是有共同点,我已经发现你的脑子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创作,实际上,我们所谈的这些问题,你好像总是在跳动,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好像那个脑子转来转去的,这是不是你的毛病,对吧,那我呢差不多也是这样,我早上起来,我脑子特别想这个想那个,好像一直在做事情,可能突然真的是,因为这个过程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就是今天这个作品怎么解决,然后它有什么问题,会有没有更好的想法,然后这个眼力怎么弄。
陈:平常这相互的过程里面,从早到晚上,你会用schedule做一个草图吗?你会写下来一些你要干的事。
凌:现在写的少了,因为现在可以借助于电脑,但是在这之前一直是写一直是画,一些小东西,因为时间一过就忘了。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经验,我画的东西呢大约三笔四笔然后写一个字两个字就完了,然后我主要是有一种记忆,我知道一个好东西不能最快的判断它。就说,我现在有一个好想法,可能我需要给它三天时间,然后三天之后,我再看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好想法是不是真正的合理,可能有时候像喝醉了酒一样,特激动,第二天,特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要学会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怎么能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就说实际上判断的是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而不是所谓的只是一个新的idea,就是说还是真正的这个东西能说明我想说的事情,所以做到这一点必须把这些东西全都记下来。
陈:也是说你今天这个布置,这个setting,这个installation,你是一想就想出来,还是受了很多骗,才达到今天的效果。
凌:这的确是用了很长时间,就是说我给我的助手吧,也是帮了我的人吧,然后我们研究半天,今天他也在,然后我很高兴他帮了我很多忙。
陈:下次帮我。
凌:对呵呵,就说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怎么才能做到这种完美。因为这个技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术,在欧洲美国glass painting,当然这个艺术家有很多人尝试过这个材料,但是呢我自己相信他没有做到我们现在这个程度,原因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也给他们说过,在中国我们可以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尝试很多很多东西,而在欧洲美国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太系统化,太昂贵,然后艺术家没有这个可能性去试验很多很多。所以这些产品我们有些需要试验三十多个。
陈:特别羡慕的同时妒忌,这是你们更大空间的去表现自己创作的能量,因为很多中国传统技术,你怎么去挖掘它怎么找出来变成一个更大的能量去表达一个更大的一种艺术的状态。因为我昨天生病了,去改东西,一个opening,Damien Hirst他提出一个新的作品是,一整块不锈钢,不锈钢上贴着个蝴蝶,也是不锈钢的,在蝴蝶中间分布着很多不同的大理钻石在里面,这个作品是1米×1米的。
凌:1米×1米的,不锈钢的,然后胡蝶在前面还贴在上面,然后有diamond。
陈:但是我跟你说,昨天我问他这个不锈钢蝴蝶你怎么做的,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个胡蝶不是不锈钢的,是活生生的蝴蝶,立体的贴在上面,用这个金属的油,一层一层漆器一样很多片,打磨这个蝴蝶,这个蝴蝶变成不锈钢的样子。
凌:怎么,蝴蝶变成不锈钢?
陈:对,这是蝴蝶,真正的蝴蝶,大概在上面涂了一层一层漆器一样的金属的,干了以后去打磨,变成一个发亮的不锈钢。
凌:噢,对对对。
陈:厉害吧。让我好生没面子,我说你这不锈钢的蝴蝶很漂亮,他说这不是不锈钢的,是真的蝴蝶,我说真的蝴蝶是不锈钢颜色的,是一层一层油打磨,他这也算是一种传统的技术,一种状态,你看它旁边另外一个装置是一个鸟,死掉的一个鸟,但是全镀金的,它这个技术是同一个技术,一层一层油然后打磨。
凌:镀金。
陈:镀金。心在跳。 当天整个最高级的场地展览,这是一件作品,他拿了两个婴儿的头,纯放的钻石。
凌:婴儿的头,婴儿的骷髅。
陈:骷髅。两个月大的,纯放的钻石。
凌:婴儿的,小孩子。
陈:小孩子。
凌:ok,ok。
陈:你看这个骷髅头,大人是很恐怖嘛,这样子,这个小的骷髅头他可爱啊,他的眼睛和嘴巴的比例是很cute卡哇伊,你看他上面放了钻石。
凌:所以西方人做事情又残酷又美好。
陈:对,爱情就是这样子。
凌:(笑)又残酷又美好。
陈:所以,怎么说,我觉得你的作品也一样。
凌:也是又残酷又美好。
陈:对,一大堆美女,但是同时呢觉得,哇,它会破坏我的一切的这样子。所以你的冲击力比我大,这是最灿烂一个光辉,冲击力最大的一个点。
凌:实际上这个呢,比方你刚才谈的Damien Hirst,我很早就见过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样子,当时他还是大学生,就是在多伦多大学。当时呢就是,实际上英国的那个当代艺术,在这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是停止不前的,就是战后到现在呢,在八十年代末就是年代初慢慢地才出了一个撒切尔第二。当时Damien Hirst是学生,他刚出头刚有名,但是是小名,然后在柏林有一个展览,特别破的一个房子,当时那个柏林墙完了以后,好多艺术家都跑到柏林区,因为柏林很便宜嘛,然后Damien Hirst也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也去看他那个展览开幕,特别破的一个房子,也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展览厅要这个灯那个灯,然后他当时就做了那个painting,就是用机器。当时他就是用非常简单的塑料布把周边包起来,然后用木头做了一个框子,然后用塑料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它那个颜色跑出来嘛,中间放这样一个原画,然后把那个油漆浇上,然后嚓一动这个画就完了。开幕的时候都是喝啤酒啊什么的,大家都看着它转啊转啊转,那天转了好多画,转完一个就拿走放在旁边再转一个,那些画却很昂贵。那个时候我去看就觉得欧洲人做事情真的和中国人不一样,他们做事情好像真的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Damien Hirst当时毕业的作品他把牛肚砍下来放在玻璃里边生蛆,然后蛆再变成苍蝇,我看那个作品特恶心,又臭。多少年之后德国一个展览把这个作品又从英国运到柏林的一个博物馆里边去,当时这个作品花了非常多的钱,因为它不能动,蛆、苍蝇会死掉,这个东西又不能去掉,他又要让它再生蛆,再生苍蝇,所以这个东西特复杂,也特恶心,但这就是欧洲人他们做事情。
陈:但是Damien Hirst也可以说是蛮伟大,因为有一次我去东京有一个group show,这个group title是关于生命,他拿什么出来展呢,他没有拿这个牛啊鱼啊这些肚子里出来的,他拿的是油画,很大的油画,我不知道是他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看他油画这么大,油画画的什么主题呢,就画的他的助理生小孩,在产房里面,画得特别好。这个就很奇怪,一方面做着很疯狂的事,同时他有一个非常传统的技术在支持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本身他是一个有实力的蛮好的油画家,对不对,所以他的蝴蝶啊你说的这些就感觉是吹出来的,可是他本身是一个真的艺术家,就是跳跃很厉害。
凌:对,还是挑战嘛。我想作为艺术家来说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挑战,你刚才也说了嘛。
陈:他不容易啊,就是已经成功在一个方面上,要脱离开来做另外一个事情很难的嘛。
凌:这个应该不怕死才行。
陈:那你做完美女之后就要做美女。你在今日美术馆有一个大的装置嘛是一个兔子,我没有机会去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当时是为什么想到做这样一个兔子呢?
凌:这个兔子实际上有一个很小的故事,我在画室里边偶然的机会有了两个兔子,我是收养了两个兔子。
陈:我以为一个是你的老婆,一个是你的女儿。(笑)
凌:没有没有,我是收养的两个兔子,这两个兔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兔子,另一个兔子没有生存下来,是真正的小白兔特别漂亮。
陈:你是买回来不是它自己走进来的吗?
凌:不是买回来的,是收养的。我非常喜欢这俩兔子的,因为特别小的时候就收养了,也不知道是公的还是母的,实际上这俩兔子都是公的。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白兔可能是因为近亲没办法生存下来一段时间之后就自己死掉了。现在这个兔子就是今日美术馆那个兔子生存下来现在还在我的画室里。它很有意思它像条狗一样跟着我们每天在我们旁边,像一条小狗一样。就是说做这个展览好多事情都是和生活有关的。秋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画室,小兔子在旁边走来走去,有大的明月,有一种很怪的感觉,突然你会想起一种这个像苏轼写的那首诗,那是在山东诸城,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无论他喝醉没喝醉,九百年前写了这么个东西,可能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喝醉了然后在特殊的环境里面出来这样一个诗歌然后永垂千古。
陈:你有没有试过喝醉的时候作画,做创作?
凌:我以前试过,现在不做这样的事情了。
陈:你觉得这样做有意思吗?
凌:我想需要尝试。
陈:可能是一种蛮好的状态去表现另外一面的内心世界,经过喝醉或者半醉的时候去做这个创意有可能是一种蛮有趣的表现。一定有艺术家这样创作吧。
凌:当然,我试过。
陈:我有相信不同音乐家在不同状态下去创作音乐,不是完全喝醉,可能是喝一点酒,音乐的节奏表达方法会不一样。
凌:对,我想这个东西会影响艺术家创作的思维,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太现实的东西不能保持长久的永恒。太现实的就是很短暂的,说简单点很世俗的。如果说这个东西不现实,它里边有很大的成分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的无法解释的神秘性。
陈:所以为什么看你画的美女,很多人感觉有一个强烈的故事在里面,是不是每一个美女都有故事。
凌:可能吧。希望如此。
陈:有时候我做设计也是这样,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但是我要尽量去表达设计师的一种艺术家的状态。我现在做很多虚拟空间,我尽量去找一些机会去做一些完全是我个人的纯艺术的创意,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夸张的装置,三百多个挂灯在天顶上面,天顶上面有一个反光的玻璃,好像浮在水上面的莲花,下面铺着的地毯反到天顶上。那我就尽量在纯艺术方面做一些自己的项目。我很喜欢跟你们这些艺术家交朋友,也很欣赏你们的生活状态,我一直在追求但是追求不了,因为我不做纯艺术,做商人,但同时我不停地再找机会做。今天我一下飞机救过来了,先看展览再吃饭。第一眼我看见几个installation,对我很有感觉。一方面我是做广告的,是做平面的,刚才有一个video就是我公司里面有一个几百年前的柜,中间的圆圈是个铜板嘛。我有看到,但是我看到,咦,就很奇怪,我看有一种默契。我可以完全体会得到你在干什么事情,因为我看的懂你的语言,对你的作品我可以体会到你真实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很大胆地说一句我看那些美女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你每一次创作的时候想的问题,经过她的眼神和嘴巴表达,你发出一个很强烈的问号。所以基本上能你每一个画都有你的一个问题在里面,是你想问我们还是你想告诉我们的。我觉得有趣的是有可能往后你重新再看你的画带着你的问题再写一个记录有可能有趣。
凌:你说同时画再写?
陈:对,因为你创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问题给自己,创作这个眼神为什么这样表达,你在问自己什么问题。
凌:我可以考虑一下。
陈: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的。
凌:实际上艺术作品有一种神秘感,神秘感有时候像我们说的窗户不能点破一样。
陈:不说出来更好。
凌: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个空间更大嘛。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做作品的时候我靠我的直觉,很多不是靠我的逻辑。这个我想设计也一样,你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这个灰,到底这个灰灰到什么程度,对不对。
陈:我说过我工作的要求跟你们的要求完全不一样,我是有很明显的答案,具体怎么放,什么形状怎么放都有,但你们就一直在完全地放开,不用想这个,是把一瞬间的想法表达出来。
凌:可能这是我们之间职业上的区别吧。我以前是画抽象画好多年,所以我强调自己有一点是出手不凡,就像李小龙一样,就是说要到这样一个程度,我要训练自己一笔下去就到位了。
陈:但你这个画不是一笔下去就干完了。
凌:对。
陈: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当我不认识你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人的性格应该画不出这样的画出来。有可能你三个星期才做完这个眼睛,但是你这个人不是这样的。
凌:所以说人不可貌相嘛。好多人提到过这个问题。有些作品在外面比如网上等等地方流传,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艺术家是谁,实际上在网上也很少能找到我的形象,寥寥的一个半个的,所以好多人看这个作品会想象艺术家的样子。有一次一个小姑娘说凌老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你是这样的,我想你是那种特别帅气的白面书生型的男生,她可能看完画以后自己想象了这样一个面貌。所以我就跟她说不好意思,我总是失恋因为我不是白面书生特漂亮的,我长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个空间,我现在也是所谓的百炼成钢,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去努力地把每个特别小的细节去充分表达出来,每个小的颜色变化等等。其实我知道我做这些全是为了我自己,我绝对不会想这个颜色发红点、发绿点,这个睫毛这样或者是这样,这些东西实际上很少有人看出来,其实是我自己认为这样最好,我要做得我自己感觉问心无愧。
陈: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我studio,我给你看我拍的你作品时的感觉吗?晚上十二点多我们去酒吧,后来到我公司去看我买的他的作品,我买的作品不是跟他买的,也不是跟画廊买的,当时我胆子很大,在苏富比看到你的画就自己拍你可能不相信,如果我没说错当天是我第一次去苏富比拍卖,因为我拿那个牌的时候手就这样子,不知道怎么拿出来的。最后只有一个人跟我在抢你的画,那个拍卖官就说还有一口吗?看着我,我这只手就…每一口是5万块钱,10万多,你的画不便宜你知道吧?因为你拍卖的起步时60万,我就跟我老婆说90万就行了,我没那么多钱去买他的画,但到最后一口是八十多万的时候我就在想该怎么办,对方说90万,我这个手就上来了。因为那个拍卖官的眼睛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诶还有一口吗我这个手就上来了,最后是我买了。
凌:不好意思,一下子丢了那么多钱啊。
陈:当时我认识这个兄弟已经有四五年了,如果直接跟你买或者跟画廊买会便宜很多,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第一首先我买的不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男生,是一系列应该是英雄系列是吧?
凌:不是,应该是宫廷仆人系列。
陈:因为我跟你交谈时从来没说过要买这个画,我从你口中知道基本上你不会再做出这个感觉出来因为已经过去了,第一我想拥有一些过去的东西。第二我真的很喜欢这幅画。第三我以前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不允许我放第三个女人在家里面。所以我就买了个男生回去。我买了这个画之后当天他来香港吃完饭我带他到公司去看这个画,我觉得当时你也是很感动,是吧?
凌:有,你知道我的眼神。
陈:我看到你的眼神看到这个画放在我的studio里面。因为是我去拍卖回来的,不是从他身上买回来的,这种感觉是我对一个艺术家的尊重。
(观众鼓掌)
凌:谢谢Alan。
陈:我再多说一句,我喜欢这个画是因为它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力,是个美男,帅哥,眼神嘴巴特别sexy,但他胆子很大,在整个画面中间有那么几笔白色“唰”地走过,做完那么完美的一幅画,你还胆子那么大去拿一个毛笔去“嘘”,这几笔做得不好怎么办。我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完美。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做完了还要破坏它呢,当然这不是破坏。
凌:这个说到底也是自我挑战吧。我有一次在访谈上也说过要么就自我超越,要么就自我毁灭。
陈:但你不做这个这幅画的感觉也非常好。
凌:但我个人感觉还差一点,就是说在一种非常完美的情况下实际上跟我们的生活的距离还是远的,所谓的谈情说爱等等实际上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实际上艺术同样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个人非常希望能不能每次作品都有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时候也很郁闷。索性算了吧不想看了吧,那种状态也不够好,这段过程也是有必要的。我在欧洲的时候有一次把画笔扔出去了,说Goodbye art!但是还是不行,第二天早上起来心里面特别不舒服,所以还是要坚持,我真的没办法放弃。就真的有一次把笔扔出去了,不画了,洗手不干了。
陈:这个画还在吗?留给我。
凌:我再想想这张画到底是在哪里,现在可能还在。就是那段时间情绪特别不好,骂人也骂不出来,就把画笔扔出去说算了不干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这个梦就是在一个边境上,要么就跳下去,要么你就站立在里面。有一种特别伤感的感觉,好像走到尽头了。醒来之后感觉心里面特别不舒服,好像没办法放弃。
陈: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让我没办法做艺术家。我因为给广告界设计界培训过来那么多年,做每一件事情一直会怎么去布置,怎么去做这个方案,怎么去影响权重,怎么去提升形象等等,都是很多数据做出来。所以我现在开始去尝试在三五年包括我在上海开展览做一些纯艺术方面的,我就觉得不是不好看,回头看就是觉得太保守,太技术,有可能心态要跳出来。你们就是很容易去跳出来,没有框框,但是我不是这样,我整个工作的调整告诉我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才打到这种效果,所以我是在一个很矛盾的边缘,就是一方面我想多做一点纯艺术但同时我又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够。
主持人: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可能来不及跟大家Q&A的环节了,还是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也看到了两位一位设计师一位艺术家他们的性情,以及创作中的灵感,以及他们对自己信念的坚持,也看到了很多凌健老师创作背后的花絮和故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陈老师大老远跑来参加我们今天这场讲座,谢谢!
来源:网易